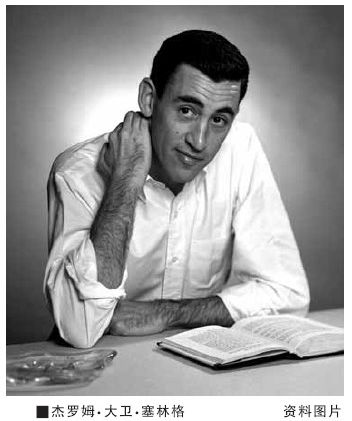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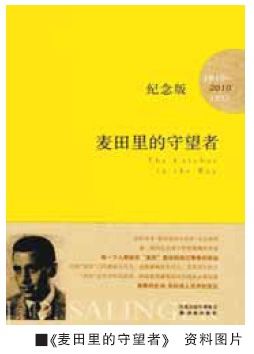
2019年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2010)诞辰100周年。他创作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作品经典之一,其作品经常会登上畅销书榜单并成为评论家追逐的热点。塞林格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犹太富商家庭,曾亲历二战,也曾拒绝过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宴会邀请。他极其注重隐私,甚少接受采访,成名后一直过着低调避世的生活。但或许正是塞林格的特立独行让他成为了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文坛的讨论热点,直至今日,“塞林格热”也没有降温。
战争创伤引发思想转变
塞林格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在婚前是天主教徒,为了能够顺利地与塞林格的父亲成婚也皈依了犹太教。但由于塞林格父亲的家族一直以来都有“反叛传统”的精神,再加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盛行反犹主义,因此塞林格的父母对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讳莫如深,甚至对自己的孩子都三缄其口,其严格程度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头便可窥见一斑:“我要是细谈我父母的个人私事,他们俩准会大发脾气。”后来塞林格一家更是割断了与所有宗教的关系,这不仅达到了家族“趋利避害”的目的,更为塞林格之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
美国参与到二战之中后,许多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被点燃,塞林格也加入了军队,他先是担任通讯兵,后被安排从事情报工作。但初入军队时的激情和理想很快就被战场上四处弥漫的恐惧和死亡气息所取代,战争让塞林格的身心受到重创,彻底颠覆了他的精神世界。而参军时的豪言壮语已经转化为“活下去”的信念,尤其在看到因为大雪融化,数量众多的美军士兵遗体在赫特根森林里显露出来时,塞林格知道他能信任和依靠的只有战友,而不是上帝。
塞林格在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细致地展现了他的思想变化:写于其参军初期的《最后与最优秀的彼得·潘》十分生动地刻画了母亲对入伍儿子的不舍;《最后一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则是对战争血腥本质的一次集中抨击和揭露;《一个在法兰西的小伙子》中的上帝已经被“一封家书”所取代;而《陌生人》则涉及了士兵所面临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总之,战争对塞林格影响巨大,各种残酷的景象让他质疑上帝的存在,而写作恰好填补了他因信仰坍塌而产生的空虚,成为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二战的结束虽然中止了肉体上的痛苦与折磨,但是心理上的创伤却始终难以愈合。对此,塞林格曾表示,“你永远也无法真正完全把肉体烧焦的味道从鼻子里赶出去,不管你活多久”。
借助东方哲学走出阴霾
二战结束后,悲观厌世、精神崩溃和信仰危机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将叛逆、纵欲和滥交等反传统活动奉为信条的部分美国人的行为,冲击着美国的精神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人开始研究东方的文化与思想,寻求精神上的归宿以及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与此同时,大量东方古代文学及宗教著作被带到美国,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传播。
塞林格从1946年末开始研究佛教禅宗的思想,当时的他已经离开战场,并刚刚结束一段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婚姻。在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和婚姻的失败后,塞林格曾有过短暂的迷茫。但在接触禅宗的思想后,尤其是在与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相识后,他内心的郁结得到纾解,明确了自己的写作与人生方向。为了能够更好地感悟禅宗的思想,他远离喧闹而繁华的大都市,搬到更为幽静的城镇居住,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打坐、瑜伽、冥想和写作。研究禅宗的思想让塞林格产生了一种责任感,那就是要通过他的小说进行一次精神上的启蒙。于是,塞林格接连创作了包含浓郁禅宗意味的《弗兰妮》《祖伊》和《西摩:小传》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对战争的指责与批判,而是对心灵的救赎与启悟。这些作品也反映出了东方哲学在塞林格的信仰重构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醉心写作抒发人生感悟
塞林格从小就对戏剧和写作感兴趣,他13岁便开始为所在学校的校刊《麦克伯尼人》撰稿。在美国福吉谷军校学习期间,他年年都是校年鉴《交叉的马刀》的文学编辑;在乌尔西奴斯学院,他不仅为校报撰稿,还在其中开创了自己的专栏。但塞林格的专业作家之路是从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其恩师惠特·伯尼特结识开始的,从那时起,他在《小说》《哈泼斯杂志》《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客》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
塞林格的写作是纯粹的。在对待写作的态度上,他明确而又坚定,在《西摩:小传》中,他就借西摩之口表示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信仰,因此真正的作家会扪心自问:“你写时全神贯注了吗?你写到呕心沥血了吗?”而这样的信念无疑会让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痴迷于名利的作家自惭形秽。此外,写作贯穿塞林格一生,在接触禅宗的思想后,他更是把写作变成了生活的全部,每天都在离家很近的“工作室”里连续写作,除了回家吃饭外,他几乎足不出“室”,因为那里不仅仅是他笔下理想的“格拉斯家族”诞生的地方,更是他寻找内心平静,进行冥想顿悟,以求获得自我救赎的所在。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塞林格可以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互为参照,如格拉斯家族中的巴蒂往往就被视为是塞林格本人在作品中的投射。也有学者认为,塞林格的“第二自我”应该不仅仅包括巴蒂,同时也包括西摩——格拉斯家族7兄妹中的大哥、整个家族的精神领袖。的确,写作已经成为塞林格生活的全部,他难以将写作与现实清醒地区分开来,而与塞林格极为相似的巴蒂的出现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但由于对禅宗的认识不断加深,塞林格虽仍然拥有巴蒂的躯体,在精神上却更趋向于西摩。因此,西摩才是他在思想上最“究极”的形态,是他一生自我救赎的终极境界。
塞林格在东方的哲学思想中找到心灵的归宿,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以“直觉”和“感悟”为手段的部分东方哲学思想更接近“人性”与“自然”,而人正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塞林格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东方哲学的适时传入让他在战后重新认识了自己,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塞林格又是幸福的,其作家身份让他能够与“理想自我”在作品中相会,在彼此角力中完善与升华。塞林格将自己的心灵感悟一次次地抛向大众,并给予读者真正的灵魂滋养。在塞林格诞辰百年之际,我们仍然能在中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塞林格的影子,其影响力已经大大超出了当时评论家们的想象。当塞林格独居森林、隐遁避世时,评论家大多认为他不过是在故弄玄虚、虚张声势,可是当他倾尽后半生凭着忘我、醉心的写作来自证时,我们知道他终于成为了其笔下的西摩·格拉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