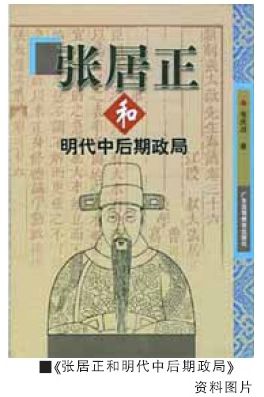
读韦庆远先生(1928—2009)的《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我有两个十分强烈的感受,一是对资料收集的高度重视,二是对人对事分析的鞭辟入里,这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的。
充分运用多种史料
正如徐泓先生在本书序中所说,这部著作既充分参考了《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常见”史料,更引用文集、笔记、书信150多种,又引用地方志65种。文集、笔记、书信中的大部分,作者是张居正的同时代人;而地方志中,明代的有43种。这不仅仅是数字问题,而是表现韦先生对“史源”的态度。所以,读这部著作时,好像是当时的人们说那个时代的故事。不仅如此,近代和当代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日本、韩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也尽收眼底。通过这部书,大体上可以知道学界的张居正研究状况和基本评价。
为了说明即使在“清算”时期,仍然有不少官员为张居正“仗义执言”,韦先生列举了左都御史赵锦、翰林院左谕德于慎行、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陆光祖、湖广副使骆问礼等人的奏疏。如果这算是“常见”资料,那么在讨论张居正与曾经的湖广巡抚顾璘的关系时,所用史料则主要有:张敬修《太师张文忠公行实》、李选《荆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徐学谟《徐氏海隅集》、傅维麟《明书》、朱怀吴《昭代纪略》、顾璘《息园存稿诗》、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以及张居正《张太岳集》中的《与南掌院吴初泉》《与文选李石塘》《答应天巡抚》《与南列卿王公》《与南掌院赵麟阳》《与操江王少方》《与南掌院周少鲁》等书牍。
张居正将自己的会试下第解释为:“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而韦先生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张居正自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举之后,张居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世致用之学,而不屑于科场的八股。科举失败之后,他发现还是得回过头来重新攻习不屑之经义,以取得功名,这样才能进入官场,发挥自己的才干。
为此,韦先生发出感慨:“中国多少知识分子在灯前窗下皓首穷经,耗费半生甚至终生的时间精力以揣摩钻研这种无用之学,无非是因为它与功名富贵密切联系在一起,无非是因为这是当时最主要的有望能显亲扬名的出路,故此自甘情愿地投入帝王彀中。专制统治的意识网罗编织得如此周密,传统的惰力又是如此强大,即使其后成为一代巨人的张居正也莫能自外。他也必须通过这条狭窄道路并用力敲开横亘在前面的扉门,才能跻上政治舞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种解释是符合真实张居正及明代现实的。不仅张居正是这样,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的王阳明(守仁)同样如此。
精彩处处可见
这部著作写的不仅是张居正个人,也希望展示当时的那个时代。因此,从体例上说,既是人物传记,又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这也正是韦先生的长处,所以精彩处处可见。
对于徐阶和严嵩的关系,特别是张居正在二人之间的周旋,以及张居正和高拱由生死之交到相互倾轧,韦先生都有合理的分析,而对于嘉隆之际政局的描述,更是精当:“在当时特殊复杂困难的局势下,徐阶是一个能巧为因应而且饶有干才和业绩的人物……但是,时代在发展,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对策亦发生变化。进入隆庆朝以后,朝野有识之士面对着自正德、嘉靖以来遗留下来的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已不仅仅满足于适度补漏除弊,而迫切要求更新,各种主张改革的声浪,正如开闸泄洪,波涛直下。徐阶以及李春芳对于这些呼声,先是愕然,后是茫然,甚至还有反感,无法接受急剧的再转折,仍然谨捧着‘恢复祖宗成法’的神幡以对付……而与此同时,高拱和张居正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高拱在其《除八弊疏》,张居正在其《陈六事疏》,都能高屋建瓴,分别提出一系列大(打)破常格,立足于变的方案,坚持变则通,通则兴,绝不应再抱残守缺。”
一代人管一代事,一个时代需要一代新的政治家。韦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仅从权力角逐的角度理解高拱和张居正的上位、徐阶和李春芳的出局,并没有完整反映出斗争的实质内容。虽然并不否认其中的权力斗争因素,却不应该仅限于权力斗争,还应有更深刻的政治内容。韦先生指出,隆庆内阁成员之间不仅有政治理念的不同,也有意识形态和学术上的对立,这既是政见上分歧的折射,也是导致政治分野的重要原因。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为主要代表,尊奉在陆九渊“心学”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阳明学”;而另一方则是口头上尊崇孔孟之道、实际上服膺法家学说的高拱和张居正,二人都尊崇实学。而“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更为微妙。一方面,两方相处,从未公开出现过任何裂痕,总是互相表示关怀、推崇和器重;但另一方面,在政治纲领和学术方向上,本来就隐藏着泾渭分明的歧异”。进入隆庆朝之后,面对新的局面,或厉行改革以辟新路,或修补旧制以求因循,二人开始分道扬镳。
在展示人物风貌、时代特色的同时,韦先生处处表现出人文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所以他特别说道:“笔者极愿秉承不诬不谀的原则,能从多层次多侧面以论述本书传主张居正。但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在评估和判断一些复杂聚讼问题时,也存在着害怕掌握不准的困惑,深感功力不逮。”另一方面,韦先生治史的立场是鲜明的:“历史最多情,它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人和事,都会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表彰;历史又最无情,它对于一切祸国殃民,逆乎潮流发展,一切奸佞污秽的人物和言行,都将给予态度鲜明的揭露和批判。”
正是因为既有这种“如履薄冰”的态度,又注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这部著作不但得到学界好评,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反映。徐泓先生称之为“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对于这些评价,我深有同感。
个别细节有待处理
由于体量庞大、内容繁多,尽管韦先生力图“从多层次多侧面以论述本书传主张居正”,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没有处理得很清楚。
比如,嘉靖十九年(1540),十六岁的张居正在湖广乡试中举;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二十三岁时中进士。从举人到进士,中间有两科会试,即嘉靖二十年、二十三年,各种记载只说嘉靖二十三年的那一次,张居正会试下第,但嘉靖二十年即中举人之后的那一年,张居正是否参加了会试,张居正自己没说,各种资料都没有交代,我希望能在韦先生的这部著作中看到解释,但也没有。
特别是传说最广、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关于巡抚顾璘故意不让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举的故事,韦先生排列了许多资料,却并没有真正梳理清楚:一,张居正是为秀才的当年还是第二年到武昌见巡抚顾璘的?二,他这一年来到武昌,是为了见顾璘还是参与乡试?三,他是否参与了那一次的乡试?四,他是否真的本应录取,却因为顾璘的爱才,阻止了他当年中举?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版)特别渲染了这件事。此事不但为明史学界所熟知,而且为喜欢明朝历史、关心张居正的圈外朋友所熟知。我认为这件事漏洞百出,希望看到韦先生的解释。韦先生根据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太师张文忠公行实》说张居正在嘉靖十五年为生员即秀才,却没有注意到其后又有一句:“明年,就省试。”由于忽略了这一句,所以韦先生写道:“嘉靖十五年(1536),居正在被录取为生员后,即在当年秋天来到省城武昌参加乡试。”但是,嘉靖十五年并非乡试年,乡试是在第二年即嘉靖十六年。而韦先生列举出来的材料,只能说明顾璘对张居正的器重和张居正对顾璘的感谢,并不能落实张居正参加了嘉靖十六年的乡试并且考官准备录取却被顾璘阻止。恰恰相反,如果顾璘真正阻止,倒是不合情理,谁能保证张居正下次就一定能中?
再如,张敬修《太师张文忠公行实》和李选《荆州府知府中溪先生元阳行状》,在张居正入官学为生员时的记载上有矛盾。当时,荆州知府到底是张敬修所说的李士皋,还是李选所说的李元阳?韦先生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没有落实,只是加了一个附记,“供参考”。如果查阅《荆州府志》,这一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在一部80万字的大书中,存在这些细微的问题,按理来说不足为怪。但是,因为这是张居正一生中带有传奇性的事件,关注度太高,所以还是有定论或者合理的解释更好。
日复一日搜集整理材料
韦先生在“后记”中,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全书结束语:“本书定稿之日,恰好是自己年届七十之期。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应该更加努力工作。”
多年前初读此书时,对这句话完全没有感觉,但这一次重读,却不禁感慨,按中国传统的算法,我也年届七十了,但并没有韦先生那种时间非常宝贵、要更加努力工作的想法。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确切地说,应该是我这类人与韦先生的最大差别,使命感没有他那样强烈。当然,即使韦先生那一代学者,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并富有使命感的,也并不是太多。
韦先生有不少学术头衔,并被多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或研究员。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没有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所以也没有办法或者根本不屑于调集人力物力去“拿大项目”“出大成果”“得大奖项”。即使在成名之后,他仍然像一个档案馆的普通工作人员、工厂的普通“一线工人”,日复一日地在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整理材料,然后亲力亲为地完成自己的著作。由于珍惜时间、努力工作,所以韦先生在完成这部著作之后,2005年又出版了《澳门史论稿》。特别是在他80岁时,又出版了比《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篇幅还大的历史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种精神,既令人钦佩,又令人汗颜。
清人刘献庭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这大概是后人给予张居正的最高评价。邹元标因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虽然落下后遗症,却坚持为张居正平反,他对张居正有八个字的看法:“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或许可以说是相对客观的评价。虽然众说纷纭,但对于张居正的总体评价,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时代和立场。当国家承平,强调社会的自由与开放、强调自我约束和道德恪守时,对张居正一般是批评的。而当国家危亡,需要有人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挽大厦于将倾、拯社稷于将覆时,对张居正一般是赞扬的,因为社会需要张居正这种想办事、能办事的人。
对张居正的研究、对他的不同评价,将长期存在。不管后人怎么评价,张居正还是那个张居正,那个只办利国利民事、不计身前身后名的张居正。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原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