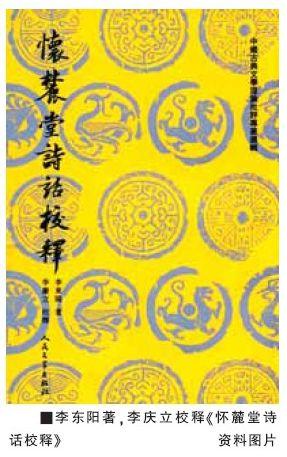
时至明代,如果从《诗经》开始算起的话,中国古代诗歌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体制,涌现出众多风格迥异的诗人,同时也形成了每个时代、每个地域独特的诗歌风貌。明代诗人面对不同体类与不同体貌的前代诗歌,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辨体,正如王廷相《刘梅国诗集序》所言:“诗贵辨体。”
以声辨诗文之别
在明代,前人最有代表性、最符合理想标准的作品,即严羽所谓的“第一义”诗歌,被抽象为基本的诗体审美规范(在“格调”论诗学那里,它往往表现为“格调”),制约着明人具体创作时的“运意构思”。此即许学夷《诗源辩体》所谓的“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明人的“以声辨体”,正是依据这种“辨体”思路而展开的。其所辨之“体”,不仅包括各种体类之体,如诗与文、古诗与律诗等,还包括各种体貌之体,如地域诗体、时代诗体和作家诗体。而明人用来区辨诗体的重要因素“声”,不仅包括具体的声韵格式,还包括在声韵格式基础上形成的音声风格,甚至包括诗歌的各种构成要素(如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经由歌咏而形成的整体艺术美感(呈现为“调”)。明代诗学中的“以声辨体”显示出明人对“声”与“体”关系的深刻认识。
以“声”区辨诗与文,是明人“以声辨体”的重要方面。李东阳曰:“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匏翁家藏集序》)“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春雨堂稿序》)“诗之体与文异……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沧州诗集序》)郝敬曰:“诗与文异,文主义,诗主声……文主理,故贵明切;诗主声,故贵温厚。”(《艺圃伧谈》)王文禄曰:“文显于目也,气为主;诗咏于口也,声为主……文以载道,诗以陶性情,道在中矣。”(《文脉》)综合以上三家之说,文与诗皆可“载道”,文重在“以义为用”,用“意义”来实现“纪述铺叙”“说理载道”之目的;诗则重在“以声为用”,取“温柔敦厚”“雅正平和”之声,“反复讽咏”,来实现“陶写情性,感发志意”(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之诗教目的。
“诗”之载道是通过“声情”的教化作用来实现的,诗歌的主要目的在于抒情,以声情感人进而“陶养性灵、风化邦国”(唐顺之《送陆训导序》),而非叙事和议论。明代诗学中对唐诗的推崇、对宋诗的贬低、对“诗史”概念的反驳大都立根于此。明人以“声”辨诗文之别,一方面抓住了诗歌自身的审美属性,凸显出“诗歌”作为“原始音乐文学”的“音乐性”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带有“以声为教”的目的,是审美性与教化性的统一。
以声辨体类诗体
“体类诗体”即传统文体学批评中的诗歌“体裁”“体制”。以“声”辨体类诗体之所以可行,正是由于“声”是诗歌区别于文的基本特征。明代诗学对于诗歌“体制”与“声”的整体关系有着明确的认识。这首先体现在明人论诗往往以“声”(声响、音响、声调)与“体”(体制、体裁、体格)二者相并列。如朱权曰:“体制声响,二者居先。”(《西江诗法》)黄溥曰:“体裁音响不能不随时以降。”(《重刊诗学权舆序》)胡应麟曰:“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诗薮》)其次体现在“以声合体”(怀悦《诗法源流》)、“体制不一,音节亦异”(朱权《西江诗法》)、“声体”(许学夷《诗源辩体》)等观念的提出上。其中,许学夷以“声体”之“纯杂”论诗最能体现明人“诗各有体,体各有声”的辨体观。
许学夷说:“子昂《感遇》虽仅复古,然终是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句……朱元晦《斋居感兴诗》,声体完纯过之。”此处许学夷以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与朱熹的模仿之作《斋居感兴》诗二十首相对比,认为前者为“唐人古诗,尚杂用律句”,后者“声体完纯过之”。许氏此论涉及李东阳的“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怀麓堂诗话》),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选唐诗序》)等重要诗学命题。古诗与律体、唐五言古诗与汉魏五言古诗在声音方面的体制规范被许学夷称为“声体”。汪涌豪认为,“不同的体式各有相对应的‘声’,是谓‘声体’”(《“声色”范畴的意义内涵与逻辑定位》),基本上切中了“声体”观念的内核。“声体”是指某一种诗歌体制在声音方面的规范和特点。因此,“声体”概念必须放置在“声”与“体”的关系中来理解,“声体”之纯杂是从“声”的角度来看一首诗是否符合该体类诗体在“声音”方面的体制规范,符合则“声体”为“纯”,反之则“声体”为“杂”。
明代诗学中以“声”来论述各种诗体的发展流变,对“古体诗”与“近体诗”具体声韵格式与音声风格的探讨,及“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等有争议的话题,都涉及“声体”这一概念。明人以“声”区辨不同的诗歌体制,虽有琐屑之弊,但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其诗体观念的精细和成熟。
以声辨诗歌体貌
晚明林兆恩曰:“余尝考其声于其天焉,天有其时,而古今异也。考其声于其地焉,地有其气,而山川异也。又考其声于其人焉,本于所习,而少成若性者异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难与言声矣。”(《诗文浪谈》)明确提出对诗声的分析要注意天(时)、地、人的区分。稍晚一点的屠隆也说:“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曹刘绮缛,潘陆富丽,江鲍徐庾工妍,李杜极材,韩柳禀法,元白尽情,王孟得趣,庐陵体洁,眉山气昌:斯声以人殊者也。周风美盛,则《关雎》《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驖》;陈曹风奢,则《宛丘》《蜉蝣》;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者也。”(《鸿苞·诗文》)此处所谓“声以代变”对应于“时”,“声以人殊”对应于“人”,“声以俗移”则对应于“地”。可见,明人清晰地认识到,诗歌整体的声音风格受到来自时代、地域、作家的影响,进而呈现为不同的体貌特征,由此可以“声”分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家的诗歌体貌。
明人以“声”辨时代诗体主要表现为李东阳的“时代格调”(《怀麓堂诗话》)说和王世懋的“时代声调”(《艺圃撷余》)说,并具体呈现为诸如古调、唐调(盛唐调、中唐调、晚唐调)、宋调(李梦阳评点《石淙诗稿》、谢榛《四溟诗话》)等一系列以“时间+调”命名的名词短语。明人以“声”辨地域诗体主要体现为李东阳“吴歌清而婉,越歌长而激”(《怀麓堂诗话》)对于吴越诗歌音声风格的区辨与徐献忠“秦楚析壤,异其商角之奏”(《唐诗品序》)对于秦调悲壮悠扬、楚调凄怆哀怨的区辨。明人以“声”辨作家诗体,首先表现为以具体的音声特点来评价诗人的诗歌体貌,如徐献忠评崔颢诗“气格奇峻,声调蒨美”,评王昌龄诗“天才流丽,音响疏越”(《唐诗品》);其次表现为基于对某人诗体音声风格和艺术风貌的整体辨识,将该作者所具有的诗体风格以“人名+调”的方式固定下来,如“太白声调”(《四溟诗话》)和“杜调”(李梦阳评点《石淙诗稿》、胡应麟《诗薮》)。
明人以“声”辨时代诗体、作家诗体,还暗含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如对于“古调”“唐调”“宋调”,明人显然褒“古调”“唐调”而贬抑“宋调”。而以作家之名命名的作家之调只见于“太白声调”与“杜调”,这表明在大多数明代诗人看来,只有李白与杜甫的诗歌格调才是最值得模仿的典范。
因此,无论是以具体的声韵格式区辨各种体类诗体,还是以整体的音声风格区分时代诗体、地域诗体、作家诗体,明人的“以诗辨体”大都包含着以此促进诗歌创作的意图。可以说,明代诗学辨别具体的诗歌体制、时代格调、作家格调,除了有面向历史的理论总结外,最重要的便是立足当下,为明人的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格式规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有典范意义的诗歌范本的反复吟咏,形成对“格调”的整体语感,从而创作出既符合体制规范,又符合“格调”之“审美典范”的诗歌作品。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明代诗学中的“以声辨体”论是一种带有“实践性品格”的理论。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诗学‘声解’传统研究”(17ZWC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