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早在使徒时代,基督教就已将中国列为其传教的目标地。及至近代,一些西方传教士更沉迷于“中华归主”、基督化中国的“美梦”。到了现当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却被普遍视作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不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性的公共论域中,基督教的中国化都成了事关基督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态势的重大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可谓让人目不暇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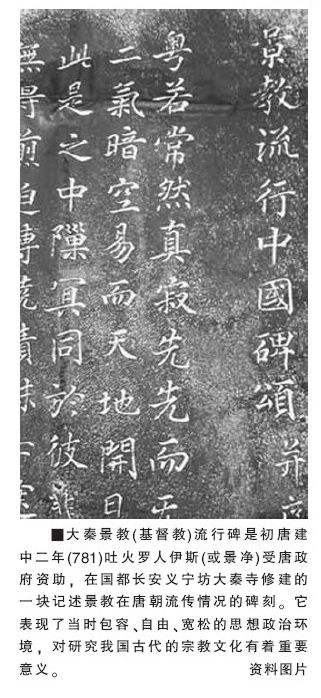
笔者想就以下几个问题略献刍荛之见。首先,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问题。这貌似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性问题,教内人士可能会断然答曰:基督教的中国化当然要由教会和信徒担纲主体角色。揆诸中国基督教历史,这种解答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例如,自景教于贞观九年入华之始,其教内精英人士就自觉全面附会和适应中华本土的儒释道,以求自身之高效的传播与发展。景教本公教之异端聂斯托利派,入华后难以命名,乃附会老子李聃之思想曰:“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以此为景教命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这分明是影射周末老子乘青牛西入流沙的传说,喻景教东来是再兴老子之教。凡此皆说明景教为求得发展,附会为李唐所攀附的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景教教士还附会外来宗教佛教,景教碑、《三威蒙度赞》等汉语景教文献屡屡援用佛家术语,如妙有、慈航、世尊等,乃至以佛称上帝,以贝叶梵音称景教经典,景教神职人员都以僧自称,更以接受朝廷所赐之紫袈裟为荣。当然,更重要的是,景教教士还自觉地附会主流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他们对信徒以尊君事父相号召,大倡忠孝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道非圣不弘”相标榜,自觉将景教置于普遍王权设置的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框架之内。这种全面的本土化确实迎来了景教的一时兴盛,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景。
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之制定人利玛窦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明确要求各宗教团体在中国须“依基督教的方式修正和适应”。他的适应策略包括以下数端:合儒斥佛,走上层路线,以皈依士大夫为切入点,进而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圈;对维系着中国大一统的重要支柱——祭祖敬孔仪式进行去宗教化的道德解释,并容忍之,以此消除中国天主教徒宗教生活中的障碍;适应中国人信奉书本上的道理和以文会友的习惯,采用哑式传教法,以中文著作传播天主教;采用科学传教法,为了满足一些儒生乃至朝廷对地理学、天文学、历法、数学等西洋科技的浓厚兴趣与需要,以西洋科技为辅助手段进行传教。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也为天主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氛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采用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本质上就是使天主教中国化。
如此看来,似乎内生动力才是助推基督教中国化的有效机制,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诚如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社会和帝国政府都会要求外来者在文化、礼仪、社会、政治和宗教等各个层面符合中国的正统。如果没有明末民间和官方人士掀起反教浪潮,批判天主教裂性、反伦、诬天,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的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致力于融合儒耶,炮制出融汇儒耶的“儒教一神论”——一种儒化了的天主教。如果没有20世纪20年代持续6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当时政府发起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很难想象由教内人士为了应对时局而倡导的自立教会运动与本色化运动能向收回教权的纵深推进。由此看来,基督教的中国化是由教会内在的传播需求或内驱力与来自社会的律令式的要求或压力这两者合力促成与推动的,忽视其中任何一方的作用,对基督教的中国化的理解都会失之偏颇。
其次,基督教中国化于何者才更有生命力、更能对中国社会文化发挥正功能?我们还是从历史资源中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如上所述,景教在唐朝全面附会中国的儒释道传统,虽然出现过一时之兴盛,但由于景教在附会佛教的路途上走得过远,又没能阐发出一套足以彰显其“要道”与“本真”的独立汉语神学,以至于唐朝与五代的史籍都视之为佛教的一支。会昌法难时,由于唐武宗的一纸毁佛诏令,景教遭受池鱼之殃,连同佛教一道被禁断。以后佛教虽再度兴盛,景教却一蹶不振,寂然无所闻见。直至明末(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时,耶稣会士才奔走相告,宣告天主教早在唐朝就已经入华流播。明末清初天主教采用合儒斥佛的传教策略,其传播与发展倒是相当“成功”,中欧文明也从由耶稣会充当中介的文化交流中受益匪浅。但在礼仪之争中,由于反对耶稣会传教策略的其他修会与罗马教廷执着于天主教的“本真”,导致康熙断然禁教。这从反面说明了若与中国主流传统背道而驰,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必定会遭遇无法逾越的障碍,导致其在华自由传播权的彻底丧失。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危机,基督教的中国化不得不一方面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高度关注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以及科学与民主等体现时代精神的论题。教会自立运动与本色化运动之所以能成为后来乃至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历史借鉴,正在于它们既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充分关注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潮与价值观,并尽力保持与它们之间的亲和性。
最后,基督教的中国化到什么程度才能令双方都受益?历史的启示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应该做到化而不消才可能赢得双赢局面。景教的过度佛化,导致其烟消云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自然令其自身与中国社会文化均无法受益。理查德·尼布尔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基督教自从产生以来,在漫长的传播历史中,形成了处理自身与文化之关系的五种态度模式:反乎文化、属乎文化、超乎文化、与文化相反相成、改造文化。尽管在某些社会中的某段历史时期,一些教派判定世俗文化彻底腐败了,与之保持高度的张力,因此获得了一时之兴盛,但这种张力与兴盛是难以长久维系的。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基本采用了保罗的基督属乎文化的态度,肯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天主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仅在属灵领域里维系所谓天主教的“要道”与“本真”,将儒耶之间的张力降至最低限度。这样,它不仅在明末清初获得了可观的传播与发展,即使在“教难”乃至禁教之后,其传承还能得以赓续,做到了化而不消。这样的本土化传播与发展曾令中欧文化都从中受益匪浅,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不争事实。
综上所述,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在教会内在需求与本土文化要求的双重驱动下,由教内人士尤其是知识精英担纲自觉主体的,既融汇中国主流优秀传统文化,又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之时代精神,同时不完全丧失其宗教“要道”的在地化运动。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目的则或许在于,一方面求得自身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另一方面又对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与文化发挥整合凝聚力的正功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