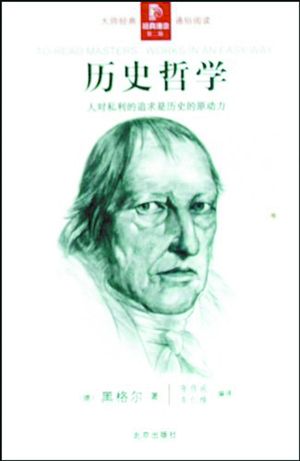
自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以来,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价值就天然地包含自由与平等这一组包含内在矛盾的概念。这种矛盾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集中体现。今天,我们有必要反思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平等是否是近代的核心价值。
《历史哲学》是1882—1831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题为“世界史的哲学”课程的讲义,于其殁后的1837年首次出版。在授课的最初(“导论”部分),黑格尔明确提到哲学的世界史的论述可以回溯到《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以下简称《法哲学》)中。对比《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后者是对前者结尾部分“世界历史”的系统性建构,进而将黑格尔关于世界史的哲学性思考,以严整的逻辑形式纳入其哲学体系。
探求“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
无论是《法哲学》的“世界历史”还是《历史哲学》,黑格尔期待解决的问题,都是基于先验的理念证明而非说明经验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黑格尔首先区隔了三种历史学,即原始的历史学、反思的历史学和哲学的历史学。黑格尔认定历史需要指明未来的必然性,即由于世界由理性支配,因此世界史必然以理性方式发展,这也是哲学的历史学最核心的工作。与此对应,原始的历史学是基于个体直观进行的表象描绘,其目光聚焦于过去业已发生的事件;反思的历史学则以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视野“超出事情本身”地进行思考与反思,试图联结过去与现在,但这种方式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历史哲学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还原真实历史,也不是以古为今用为目标,而是从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中,探寻“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
以指明未来的必然性为目的的历史学,其研究对象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展开的必然过程。因此,努斯式的不“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理智”必须被排除出精神和世界史的范畴。对于黑格尔而言,作为主体的精神需要意识到自身自由,这种自由的意识不断发展并在现实中形成作用,而这就是世界史的本质。从这个定义看,世界史的核心是支配世界且自在自为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必然是自由的。换言之,在黑格尔的观念中,理性与自由是不容辩驳的核心价值,而对自由的认知程度,又反过来证明个体、民族、文明乃至国家理性的水平,这也成为他“世界历史之自然的划分”的依据。在此观念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人知道特定的部分人是自由的,唯有日耳曼人真正知晓“所有人绝对是自由的”,世界史也因此被自然区隔为东方的历史、古希腊的历史、罗马的历史和日耳曼的历史四个阶段。
不平等具有合理性
黑格尔的这一论断一定程度上与经验一致。但不能忽略的是,在逻辑结构中结论和前提的差别;同时,这一论断还包含两个问题:第一,被意识到或“知道”的自由是什么?第二,对于自由的认知程度不同会有什么结果?至少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并未对自由进行定义,也未设定其边界。这样的含混拓展了黑格尔论断的适用范围。为了厘清黑格尔此处所言的“自由”,我们可以参照他其他著作,或是基于自身的理解进行回答,但这弱化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关心,从而忽略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包含的不平等要素。
如果我们相信黑格尔的论断,并以此为前提,自然就会接受他所说的东方—古希腊—罗马—日耳曼的历史线性序列,这个序列包含着原始的历史学、反思的历史学、哲学的历史学的演进,同样也包含东方—西方的区隔。古希腊—罗马—日耳曼的路径在经验事实中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在探讨日耳曼民族的文明与思想时,古希腊文明业已衰亡。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其民族与历史和西方民族、历史是一个共时性存在,日耳曼民族兴起、繁荣时,延绵的中华文明仍在持续,那么,将东方民族及其历史置于古希腊之前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哲学》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法哲学》似乎暗示了答案:“统治的民族”承担着“世界精神的自行发展着的自我意识的进程”的使命,因此作为“文明民族”的统治民族可以(甚至应当)以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意识看待落后的其他民族,民族(及国家)间的战争和争端会因世界精神的缘故而被赋予“世界史的意义”。从《法哲学》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视域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基于精神实现自由原理的过程,而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不过是某一具体民族(国家)与这种精神契合程度的区别,这种区别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平等。基于对自由认知的不同,民族及国家间的不平等具有“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的驱动下,一个民族无论其自愿与否、是否期待真正的自由,均有可能被合理地取消延续的资格与必要。
反思启蒙逻辑
黑格尔将自由与平等置于对立位置,成为一组非此即彼的选项。他并非不知道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但在《历史哲学》的论述中,他一方面肯定法国民众接纳了这一组理念,另一方面却基本忽略平等观念的世界史意义与价值。出现这样矛盾的根本原因,乃因为黑格尔以理性与自由作为世界史的核心价值。
承接启蒙运动余绪的黑格尔,之所以否定平等而捍卫自由,根本原因在于启蒙逻辑中内含的不平等要素。启蒙的核心价值是理性,而理性被假定为所有人都具有的属性,这是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但在启蒙者—被启蒙者的身份区隔中,启蒙者意味着率先自由地运用理性“摆脱自身的未成年状态”(康德语),勇敢地去思考;而被启蒙者则无法意识到自身理性。启蒙者的任务并不是灌输或传递业已形成的知识或观念,而是启发仍处于“未成年状态”的人们进行自主思考。从前提和目标看,人都具有理性,且人都应当自由地运用自身理性思考,在抽象的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但启蒙者先于被启蒙者拥有思考的能力,需要指导被启蒙者。那么,在现实层面,人就是不平等的。启蒙逻辑是否要求启蒙者承担启蒙被启蒙者的责任,以最终消除这样的不平等,或许有诸多不同答案。但就《历史哲学》及历史现实看,“启蒙者”们在理论建构及实践中,实质上利用了这种“不平等”,通过武力的方式不断扩大自身的“自由”。
正如《历史哲学》日语版译者长谷川宏所言,黑格尔历史哲学基于欧洲近代经验而确立。作为欧洲近代经验的一个总结,且以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为目标,它对理性、自由的宣扬,对平等的无视乃至抹杀是需要反思的。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正是黑格尔所言的理性意识到自身的自由,并不断发展自由,那么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自由”但不平等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如何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不平等要素,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最为关键的;而尝试分析、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只是这项工作的第一步。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