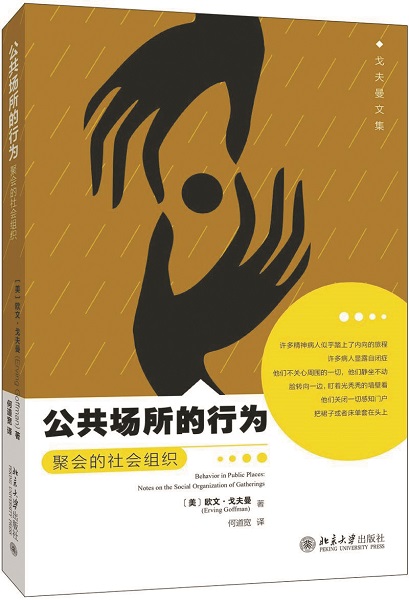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是情境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戈夫曼研究了社交场合中的行为规则,认为在日常社会交往中存在一整套情境性礼仪作为交往的规范。这些规则礼仪框定了交往参与者的小圈子、小社会,规则指引行动者的社交行为,也划定了社交边界。边界之内的行为可以接受,超出边界之外则被群体所排斥,相关行动者也就无法享受群体圈子的归属感,而对违规者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关进精神病院。
精神病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不当行为人,而戈夫曼研究的重点在于情境背后的社会规则。在戈夫曼之前,社会学研究尤为关注社会骚乱、集体恐慌等集体行为,忽略了对一般性社会交往的考察。受到精神病学研究的启发,戈夫曼对公共场所中“不当的行为”进行了观察。戈夫曼认为这样的考察有助于社会学去探究日常交往的模式与结构。他从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公立精神病医院和设得兰岛的参与式观察中获得一手资料,并以中产阶层的礼仪手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比精神病院和一般公共场所的社交行为,戈夫曼总结出公共场所交往行为的三个主要特征:交互性、情境性和规范性。
交互性
戈夫曼所说的交互性与库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传统一致,它体现在个人理解与接受他人的态度上。戈夫曼把公共场所的行为分为两大类:无焦点互动和有焦点互动。匆匆一瞥、擦肩而过等比较松散的互动是无焦点的,而围绕某个问题、某个人进行的紧密互动则是有焦点的。面晤、邂逅等面对面的有焦点互动具有显而易见的交互性,这是传统社会学考察的范围。戈夫曼对无焦点互动的考察,扩展了交互性的社会学内涵。
只要进入公共场合,就很容易进入无焦点的互动。无焦点互动的涉入在人的体态习语方面体现最明显。个人进入公共场所时可能并不会与他人进行言语交流,却无法不进行体态交流。在无焦点互动中,人人都会通过体态习语与他人进行交流,仪态举止就是交互性在公共场合的体现。与米德区分有意义体态和无意义体态不同,戈夫曼眼中的体态并没有“无意义”的类型,因为“习语对行为者和目击者都唤起相同的意义,行为者用它是因为它对目击者有意义”。
戈夫曼认为有意义的持续交流并不是典型的社会互动,很多时候行为人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印象,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自发性涉入。自发性涉入、自我专注的活动以及礼貌性忽视,在戈夫曼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交互性的特征。自发性涉入背后有一种基于印象管理的交互性在起作用,这类活动在米德的理论中并不被社会学范畴所涵纳。自我指向的人体活动,如剔牙齿、修指甲、打瞌睡等并不会指向他人,所以也不在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互动框架之内。戈夫曼认为公共场所赋予互动以一定的情境,在情境之内“自涉入”的行为具有潜在的交互性。
礼貌性忽视也体现了一种交互性的张力。礼貌性忽视介于盯着人看和视而不见之间,既给在场者充分注意,又不过度关注对方。礼貌性忽视只是传达自己注意到对方的存在,而自身的注意力却保持交互性弹力,随时可以撤回自己这里。另外,防涉入、开小差、出神、告别等行为在戈夫曼的整合下,也具有了理论弹性。这些不具备交互性的活动作为交互性的理论参照,实现了戈夫曼理论建构的闭环。
情境性
戈夫曼将公共场合的互动行为放到社会情境中进行考察,“合乎情境的活动”是其主要考察对象。他将情境界定为“人们聚集时总体的空间环境”,凡是能够进入这一空间的人员都是情境中的一员。所谓合乎情境指的是置身于情境的涉入中,而不是在情境中活动。置身于情境和在情境中的区别在于,前者所体现的社会学主张声明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情境不再像“在情境中”一样作为背景而存在,而是作为参与社会互动的主要社会学元素得到彰显。
戈夫曼描述了不同的社会情境:家庭情境、俱乐部情境、阶级情境、民族情境、文化情境、地域情境等,认为个人对情境的归属,超越了家庭、文化、阶层等社会学要素。以文化情境为例,他列举了不同文化与同一文化不同时间的差异对于理解社会互动的影响。戈夫曼提到不同文化对待演出的态度有很大一部分是行动者表达涉入的一种体态习语的差别,并不能算作参与互动本身的差异。东方观众以松散的形式观看演出,同样是在剧场这种社会情境中进行互动,只不过他们互动的形式并非以美国观众熟悉的体态习语进行而已。戈夫曼绕过传统社会学要素的干扰,从情境的一般性特征出发认识人际互动,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互动的内涵,毕竟很多互动与规则是不同文化群体通用的。
在戈夫曼看来,退出社会互动就是退出社会情境。不管是从社会共同体和社会机构中脱节,还是对社会关系的疏离,都是对社会情境的疏离。这一点在戈夫曼对精神病人的观察中尤为明显。他认为,表现出情境性失当行为,不能说明行为人就是病态的。所谓的精神病人犯的不过是一种情境性错误,这并不足以支撑精神病学的病理性诊断。戈夫曼的情境社会学对传统精神病学的理论观点和传统社会学的区块分割式构架提出挑战。戈夫曼抽象出情境这一概念,避免了传统社会学对个人、群体、文化、阶层等粗线条的划分方式,为重新整合社会互动提供了理论工具。
规范性
戈夫曼提出,人总要归属于某种群体,也就是归属于某种带有规则的情境。这种归属性为社会结构提供了制度化纽带,借由社交聚会提供的制度化纽带,从互动观点过渡到“基本社会结构研究衍生出来的观点”。戈夫曼在公共场所的观察是为了将个体的行动与社会结构进行勾连,进而解释“社会如何成为可能”这一传统的社会学之问。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依赖于社会规范性的确立。
戈夫曼对参与社会互动时的涉入分配规则、涉入对象规则以及相互涉入规制等的描述,体现了公共场合社会互动的规范性。在涉入分配的规则中,他区分了主导性涉入和从属性涉入。不同的交流条件、社会情境会出现交叉重叠,这就会造成交流秩序的混乱。为了厘清规范性混乱,需要确立一种主导性的交流秩序。主导性交流秩序要求确立情境性规则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用以维持交流的边界和秩序。被严格管理的从属性涉入为主导性秩序提供了规范的弹性空间。
戈夫曼对互动规范性的理论重视,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倾向。他反复强调个人的情境行为与公共场合的社交互动,受到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指引。交互性与情境性最终要为规范性服务,情境互动所涉入的结构才是戈夫曼真正关心的理论归宿。虽然戈夫曼主张的具有松紧度的结构不再像传统社会学区分正式互动与非正式交往那样僵硬,但是在社交聚会中寻找背后的“一般社会结构特征”,仍是他的终极理论追求目标。
显化秩序
戈夫曼对公共场所交往的考察,廓清了我们在日常交流中习焉不察的情境规则。其理论关切落脚于社会规则规范对社会整合的作用。这是戈夫曼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理论情怀,在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内,他始终观照人与人的互动。他注意到“有些行为古怪的贵族犯下了许多情境性错误,却没有被称为疯子”。这与庄子对“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观察具有同样的人文倾向,他们都对表面平等背后的结构性失衡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戈夫曼提醒我们,只要对情境性规则深入探究就不难发现,精神病学和传统的社会习俗对精神病人的观念是不成立的。戈夫曼用情境社会学为被污名者提供了理论赋权的机会。
通过情境性对社会学传统分类方法进行重塑,戈夫曼的努力具有强烈的理论开拓魄力,这与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提出“场论”更新学科架构有异曲同工之处。家庭、阶层、文化等传统社会学单位,均可被看作一种社会情境。同样,所有的社会情境都可以看作一个“场”。“场”的理论意义在于一种生命体验的整体性,这在戴维博姆的对话理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从对话的角度来看,戈夫曼的理论关注焦点集中于显化秩序,而没有深入挖掘潜在秩序。潜在秩序涵盖了包括时间、空间、运动、因果关系、普遍性等在内的基础性结构。潜在秩序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场将人与人的互动罩住,我们需要对这个无形的罩子做更加细致的理论剖析。这需要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共同努力,因为交互、情境、规范不只具有社会学意义,同样也带有很强的传播学特性,这在精神对话和情感连接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