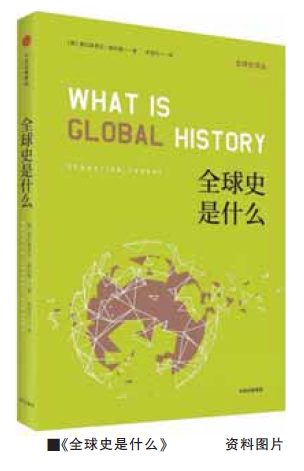
作为仍然在成型和发展过程中的海洋史和全球史,二者似乎仍处于开放性吸纳阶段,很难涵括相关内容甚或描述所谓的全貌,尤其是这两个领域均呈现出一定的方法论特质,而非纯粹的专门史学科内容。
海洋史与全球史的概念与范围
广义而言,跟海洋有关的人类的历史性活动均可以进入海洋史研究的范围。全球史则以全景式的全球史、联系的全球史、整合的全球史为三类主要取径,该观点已由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是什么》中具体阐明。
海洋史常以海疆、海权、文明、殖民和移民等相关主题为学界内外人士所熟知,而全球史主要着重“比较、联系、整合”三大面向,更强调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纠缠。海洋史与全球史是否存在交叠的领域,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大多数业内学者有这种直觉,但具体在何处产生交叠、交叠领域的研究具体又如何呈现,则基本语焉不详。目前所见,更多是将其作为两种各有所侧重的方法和视角来展开,其跨海联系或涉海部分成为核心交叠领域,若该部分仅为背景,则基于所讨论的主题重点阐释全球性的联系或影响,成为全球史的核心议题。
海洋史本身就是“全球”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本来就处于一个流动而联通的水域中,只是因为人类活动和竞争、知识的限度,海洋的历史常常被理解或呈现为区域性的历史,甚至进一步被局限为海疆的历史。如果说全球史的核心方法论是“整合”,海洋史的核心方法论则是“联系”,即便是海域史的研究也要定义或考虑“域外”,海疆的研究亦关乎另外一方的活动,海洋经济的研究也无法脱离陆地而存在。全球史可以是“海洋”的也可以不是,基于“比较”的全球史常常是原有国别史、比较史的延伸,无论是“国际法”“政治体”还是“革命”,都基于原有主题展开。而基于“联系”和“整合”的全球史则通常与海洋相关,即便是医疗和环境类的主题,跨海亦常作为一个背景存在,从枪炮、病菌到桉树和畜力。
全球史在中国方兴未艾,不少名家均着力推动这一研究进程。然而,全球史与海洋史的模糊地带并未消除。翻译出版的米夏埃尔·诺尔特《海洋全球史》即是一例。该书德文原名为《在港口与地平线之间:海洋的世界史》(Zwischen Hafen und Horizont: Weltgeschichte der Meere),中译本除了将“世界范围”进一步强调为“全球”之外,还将其直接突出为主标题以吸引读者。如此处理自然也有不利之处,即中文语义上有一种类似新的“海洋全球史”或“全球海洋史”的概念误解。在海洋史和全球史仍处于开放性定义和多重内涵的当下,合并二者显然会带来更多的概念困扰和误解。
在全球史的实践中,无论是转移史、跨国史还是“空间转向”,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均有实践和佳作,尽管仍不是全球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而在海洋史的实践中,将其放在全球史框架或视角下展开,或至少在海洋研究议题中体现全球联结,则相对容易操作。笔者即将出版的《瀛寰识略:全球史中的海洋史》一书,即采取这种方式。本书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与太平洋”“全球史与海洋史”三部分,是关于世界范围内各种“联系”的历史,既包括东南亚与中国、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块纵横经纬的交互内容,也涉及在海洋史和全球史框架下发现的时间、空间和人事,分析了环南海研究的理论和材料、早期西荷东亚扩张的竞争与冲突、中国与东南亚互动、印度洋史书写模式、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东亚海上贸易世界、太平洋时代的概念、太平洋世界移民、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野、研究导向、观念变迁等问题,以海洋史的议题贯穿始终,间或浮现全球史的视角和关怀。以这种方式书写海洋史,虽非每一篇都跟全球史相关,但只要时刻保持全球联系或区域比较的意识,即可较好地结合二者进行海洋的全球史书写实践。
海洋史与全球史的结合
海洋史与全球史的结合,即世界史领域或全球范围内(并非“全球史”)海洋史的运用展开。前述诺尔特《海洋全球史》一书的谋篇布局就很值得借鉴。是书从“发现海洋”开始,循北海、波罗的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南海,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早期到中古时代人类海上联系的画卷。转入近代,又从地中海开始,揭示北海、波罗的海、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之间的商贸、竞争与掠夺,最后以现代技术切入全球化和挑战收尾。
通览这种从世界史角度讲述海洋历史的作品,不难发现若采取“满天星斗”式的书写方式,一一论述世界各地的海洋发展历史,不仅力不从心且有流水账堆砌的嫌疑,更不是当代学者追求的“全球史”。而如果采取单点起源论述或传播角度的写法,又不免落入西方或东方中心的窠臼。以“转移史”和“联系史”的方式,对于书写的要求和尺度的把握极高。
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海洋一直存在着令人恐惧的跨界力量。雅典取得海上霸权之前,克里特岛有令人生畏的“米诺斯”(克里特之王),成为岛外各邦的中心和枢纽。而克里特岛模式的原生代,当数基克拉泽斯群岛,那里的先民用独木舟维系着岛屿和大陆间的联系。人类与海洋的联系既是天然的,又是后期不断加强的结果,而后期的这种过程并非必然,全球各地的人们与海洋联系的深浅千差万别。
海洋史研究在世界史范围的展开,如果要克服书写成通史的平铺直叙,就需要重点突出哪些转移或联系至关重要。8世纪瓦良格人以北欧为据点向南活动或向拜占庭掠夺,与9世纪维京人的活动或对里海、黑海的袭扰模式可谓如出一辙,这种航海及拓展的图景有助于改变我们对斯拉夫人、波罗的人、芬兰人等斯堪的纳维亚到伏尔加河一带活动人群的刻板印象。之后两个世纪,福斯塔特(开罗旧城)犹太藏经阁书信又很好地展示了中世纪犹太和穆斯林商人从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到印度洋的经略。14世纪开始,马木留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东地中海和黑海的扩张,又完全改变了西地中海的政治经济生态,无论威尼斯还是热那亚的强势话语叙事在黎凡特新兴贸易强权的视角下都会发生变化。荷兰人对南欧的投资以及海运行业的强势介入发生在其亚洲扩张之前,以东印度群岛的胡椒和香料打破威尼斯或黎凡特垄断的论述在时间节点上值得仔细推敲。法国在17世纪后期开始对荷兰在奥斯曼市场的挤压是另一种变化,希腊船只和船长周旋于奥斯曼、俄罗斯和西欧国家之间,则成为18世纪以来地中海及其与世界联系的“潜流”,影响及至今日。这些看起来“另类”的海洋史也是葡、西、荷、英海洋强国迭代兴起和欧洲扩张书写模式的有力补充。
这些转移或联系运用在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研究上也同样成立。印度洋的论述似乎长期以来更多在于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和印度沿岸与葡、英、法、荷产生的纠葛;太平洋的历史书写重在南太平洋诸岛和檀香、水獭(毛皮)和海参;大西洋的书写从来都与糖业、海盗还有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相联系。除去这些重要的议题和内容,勾勒那些被忽略的海岸及岸上的人和事当然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些联系和转移的重构意义非常重大。例如,马六甲作为节点,因为葡、荷、英的争斗,兼以对西文材料的依赖,与荷属东印度一样,常被归为印度洋史部分或延伸,而非现代地理节点划定的太平洋一方;利马早期的经济和人事均为大西洋史的一部分(大帆船贸易的主角仍是阿卡普尔科),只有在19世纪引入日本和中国移民的历史和论述时,才似乎产生了与太平洋的联系。材料和视角的变化对历史理解和书写的影响可见一斑。此外,不论是阿巴斯、苏门答腊西部还是作为边缘地带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是在体制内外游走的劳伦斯·戴维松和胡贝特·胡戈(商人、海盗、逃犯、海军指挥官、商站主管等)、活动贯穿三大洋的威廉·丹皮尔(农民、商人、科考员、海盗、学者),海洋史研究议题总能赋予这些另类连接更多活力,从而展现出具有全球史方法论意义的书写。我们憧憬着这些议题和实践能更丰富多样,海洋史和全球史研究也能齐头并进、不断交叉,最终酝酿生成新的理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三宝垄和井里汶编年史译注研究”(20VJXG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