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世诗风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儒家经世精神作用于诗歌而形成的诗学潮流,具体到创作层面则表现出变风、变雅的基本形态,反映了介入现实、参与历史的思想内涵。就发展走势而言,中国古代的经世诗风又呈兴衰更迭的消长之势。清代的经世诗风,因时而化的嬗变脉络亦渐清晰,政治倾向、现实属性和学术色彩尤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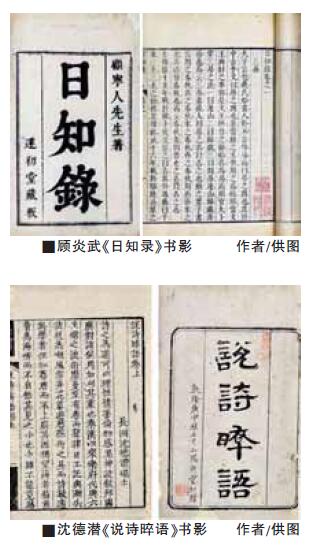
今四海干戈未宁,独风诗为盛
以探讨明亡之因为契机,以经世精神应对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和人心浮诞的世风,是清初有识之士最为强烈的学术呼声,这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诗坛。
清初诗人对明中后期以来空疏肤廓之风多有不满,公安派的浅俗轻率、竟陵派的幽深孤峭同样成为他们批判的对象。作为清初诗坛最具时代底色的群体,遗民诗人大都怀抱经世之志,推扬求真务实的创作精神是他们的用心所在。在学术层面,顾炎武于《答徐甥公肃书》中提炼了以“鉴往所以训今”的治学门径,在文学层面则于《日知录》中提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主张,以为“《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并于《与友人论门人书》中表达了对不学“五经”却耽于“白沙、阳明语录”的“今日之诗”尤为反感的态度立场;黄宗羲以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为理论依据,先后于《姚江逸诗序》《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发出“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以诗补史之阙”之论;名列清初“海内三遗民”的徐枋,其《周玉凫仪部读史诗序》则以“惟存贞臣逸士忧时念乱,流连讽刺之辞,为足观兴亡、备鉴诫”衍释“尼山采列国之风”之旨趣。凡此种种,大抵是以史家意识推阐诗之经世功用。
清初的贰臣诗人和国朝诗人,大多有过易代兴亡的创痛经历,受当时学风的影响,经世精神同样冲击、浸染着他们的心魂。被目为贰臣之首的钱谦益,亦有诗坛祭酒之誉,其于《胡致果诗序》中声称“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史为诗之本乃其论诗要旨;吴伟业虽以诗人自许,却于《且朴斋诗稿序》中肯定“古者诗与史通”说,而以“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论“天子采诗”“太史陈诗”的价值;入清为官的施闰章,博通经史,深悉史与诗有“重褒讥”与“兼比兴”之别,然于诗之用又有“有大于史者”之识,这也是其《江雁草序》所表达的核心观念;以“神韵”号召诗坛的王士禛,并未抹杀诗“可观”“可怨”之旨,于诗之“感时纪事”的作用亦了然于心,这在其弟子郎廷槐所编《师友诗传录》中尚有确切的记载。
呼应求真务实的诗学追求,清初诗坛的经世诗风一度高涨。有感于“历沧桑、遭变难”后的诗坛景象,曾灿《过日集·凡例》慨然以“顶有感天地而泣鬼神者”论,施闰章《毛大可诗序》亦有“今四海干戈未宁,独风诗为盛,贫士失职之赋,骚人怨愤之章,宜其霞蔚云属也”之识;宋荦为卓尔堪《遗民诗》所作序,则以“几与德祐、祥兴诸君子争烈矣”论“胜国遗民诗”;至于钱谦益《后秋兴》、吴伟业《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等系列作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则分别给出“实为明清之诗史”“可备一代诗史”的美誉。概而言之,故国的覆亡和时代的剧变,既促成了清初诗坛的群体纷呈,遗民诗人、贰臣诗人与国朝诗人鼎足而立,也营造了多元耸动的创作风潮,以诗经世自是最强劲的一股。
经世先王之志衰
康熙中后至乾嘉,诗歌流派迭起,又以格调、肌理、性灵为主流。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和以翁方纲为核心的肌理派,代表官方意识,主张每契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创作即便有现实的反映,表现亦偏于温和。诚如潘务正《作为讽喻的事件——沈德潜时事讽喻诗考论》所言,沈德潜论诗有复古倾向,虽偶有时政讽喻之作却以醇雅为形貌,乾隆散馆入仕被树为诗坛典型后,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又成其表达之主体,对怨刺传统多有规避,其复古已非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古道。翁方纲的肌理说,学问、义理并重,其诗关注现实的力度则显薄弱,朱庭珍《筱园诗话》讥讽他“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实缘于此。袁枚论诗主性灵,有底层化的倾向和表现,于“格调”“肌理”均示不满,其《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称“性情之外本无诗”,重个体情感的发抒而有否定“温柔敦厚”诗教的意趣;正因如此,其诗重自我表现的特点明显,对义理和现实的关注则欠密切,难免有章学诚《书坊刻诗话后》所谓“纤佻浮薄”之表现。
此外,以“道与艺合”审视诗歌优劣,将袁枚、厉鹗等打入“诗家之恶派”的桐城派宗匠姚鼐,一如吴嵩梁《石溪舫诗话》所论,其诗“有标格,正而能雅”,极尽忠孝伦常之义,不过负怨刺之旨亦深;作为乾隆朝维护风雅正统的教主,纪昀尝于《俭重堂诗序》中呼吁诗当“不乖于温柔敦厚之正”,其诗亦有《晚晴簃诗话》所言之面相,或“华贵典赡”,或“韵节和雅”,无论穷达,“蕴福尤厚”,只是经世气度又因此而趋于缺失。这样的例证,当然还有很多。要而言之,迟至清代中期,“温柔敦厚”的创作风尚已经取代经世风尚成为诗坛主潮。
何以如此?这与王朝统治的稳固、国力的强大相关,与清代的文治策略尤有干系。终清之世,为巩固政权,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并施文化高压之策,大兴文字狱,康雍乾嘉四朝称烈。同时,帝王们亦充当起风雅鼓吹手。如乾隆帝论诗,看似亦重经世,尝作《杜子美诗序》,以为“子美之诗所谓道性情而有劝惩之实者也”,然实以有利王朝统治为鹄的,以无碍“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前提。这难免约束诗人的心灵自由,挤压他们的创作空间,迫使他们以李祖陶所说“伣伣伈伈,如在云雾之中”的姿态应对天下利病,在客观上弱化了诗歌关注社会的力度,表现出“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的创作病态。而据《与杨蓉渚明府书》,如此病态至迟至康熙中期即见端倪,王士禛的神韵诗便有空疏不实之弊,赵执信《谈龙录》“诗中无人”之讥即由此而发。揆之乾嘉,经世诗风趋于式微则更见明晰,章太炎《訄言·清儒》以“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概括这一时期学术、政治与诗风之关系及表现,不无道理。
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
进入晚清,内忧外患频起,太平之象顿逝。因由时局的感染,自上而下,经世向风,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之谓,正因此而发。相应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一度低沉的经世诗学亦再度兴起。
以道咸时期居庙堂之高的翰苑诗人为例,一如曹籀《定庵文录题辞》所说,像龚自珍那样“取法《诗》与《春秋》”而发为“美恶劝惩之义,是非贬褒之条”的经世文士,自不在少数。其著者如“出入侍从”的陈沆,魏源《简学斋诗集序》认为其诗本该以“盎然春温而醇浓,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庙易山林”为特色,却给人“清深肃括之际,常有忧勤惕厉之思”的印象;身居清要而位及二品的姚元之,《晚晴簃诗话》称其“文翰从容,雅负时望,诗俊亮有格,亦多寓感时纪事之作”,“令人作贞元朝士之想”;官至礼、刑二部侍郎的黄爵滋,以经世为职志,诗亦信守其《秩林诗序》“适于用”的主张,显现出饱满的经世色泽,洪齮《仙屏诗屋诗录跋》称其举凡“生平之事功、学业悉于是而寓”,断不染时下波靡不实的“榛芜之习”。确切地讲,也正是在这些来自“都门”“谏垣”和“翰林”诗人的推毂鼓吹下,最终营造了金安清《水窗春呓》所说的“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的热闹场面,续写了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灿然景象。
在晚清经世诗风兴起的过程中,中下层诗人同样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姚莹、张际亮这对桐城派诗人即可称典型。姚莹号称“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尝于《复杨君论诗文书》中强调为诗非“徒一韵之工,争一篇之能而已”,又于《康輶纪行》中表达否认诗“无情而作,无才而作,无为而作”的意见,亦曾借《黄香石诗序》《孔蘅浦诗序》对风靡一时而在他看来却有悖“兴观群怨”之旨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试律诗发起猛烈攻击;相比其师姚鼐诗之“正而能雅”,其诗多奏风雅变调,确有郭则沄《十朝诗乘》所谓“具见忧时之抱”之颜容。张际亮虽未曾入仕,以忧国之心发为“志士之诗”却是其夙愿,其诗甚至被何长载《松寥山人诗集序》视为晚清经世诗风之“嚆矢”“肇始”,拿它媲美《长庆》《渭南》。据姚浚昌《先府君姚莹年谱》,他们又与汤鹏、朱琦、叶澧这些来自翰苑的经世文臣,同声相应,“以诗相驰逐”,遂成一时之气象。李慈铭《越缦堂诗话》则指出,张际亮“极负时名,诗亦规抚作家,而粗浮浅率,毫无真诣。尔时若汤海秋(鹏)、朱伯韩(琦)、姚石甫(莹)、叶润臣(澧)所作,大氐相同,时无英雄,遂令此辈掉鞅追逐,声闻过情,良可哂也”,批评他们的创作,文辞乖张粗粝,违背“温柔敦厚”之旨,这实际又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有为而作的艺术趣味,印证了经世诗风在晚清的再度兴起,及他们在此风尚中的主导作用,堪称近代文学救亡思潮的先声。
作为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经世本来就是一种惯常的存在,只是当它具体反映于诗坛则有峰谷之别。综上而言,自清初延及晚清,经世诗风即呈现消长之势,这当然每与清代的政治、现实和学术密切相关,又是不同阶层的诗人合力作用的结果。循此,既可觇清诗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方向,又颇可寻绎诗以经世背后所涵容的历史文化信息,并以此为依凭推阐文学经世,以赓续和发掘它的当代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清诗发展嬗变研究”负责人、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