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六年来,德国学界掀起一股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潮。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20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极大促进了相关出版物的骤增。这里仅举几例,如米歇尔·宽特(Michael Quante)和戴维·P. 施韦卡德(David P. Schweikard)的《马克思手册:生平、著作与影响》(Marx-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2016)、米歇尔·亨利希(Michael Heinrich)的《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Karl Marx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2018)、德特勒夫·冯德(Detlef Vonde)的《在街垒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失败的革命”(1848—1849)》(Auf den Barrikaden - Friedrich Engels und die “gescheiterte Revolution” von 1848/49, 2019)、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和英格·施蒂策勒(Ingo Stützle)编辑的新版恩格斯《反杜林论》(2020)以及相关文集、埃伯哈特·伊尔纳(Eberhard Illner)编辑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红黑变色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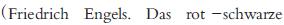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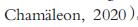 。尽管其中的一些出版物利用了MEGA2文献,但很大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不同方面,而没有特别关注MEGA版本或MEGA研究。
。尽管其中的一些出版物利用了MEGA2文献,但很大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不同方面,而没有特别关注MEGA版本或MEGA研究。
就针对MEGA的具体研究而言,正在开展的争论通常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x-Engels-Jahrbuch,简称“MEJ”)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集刊新丛》(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简称“MEFNF”),偶尔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Zeitschrift für marxistische Erneuerung,简称“ZME”)。除了期刊文章,另有五本著作直接涉及MEGA研究,包括马提亚·伯伦德(Matthias Bohlender)编著的《搏斗式的批判:马克思的作为政治使命的社会批判》(Kritik im Handgemenge.Die Marx’sche Gesellschaftskritik als politischer Einsatz, 2018)、哈根·克莱默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新视域:MEGA》(Neue Perspektiven auf die Politische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新视域:MEGA》(Neue Perspektiven auf die Politische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2019)、乌尔里希·帕格尔(Ulrich Pagel)的《唯一者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月革命前夕的启蒙话语转变》(Der Einzige und die Deutsche Ideologie Transformationen de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2019)、乌尔里希·帕格尔(Ulrich Pagel)的《唯一者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月革命前夕的启蒙话语转变》(Der Einzige und die Deutsche Ideologie Transformationen 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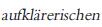 Diskurses im
Diskurses im  2020)、马提亚·伯伦德(Matthias Bohlender)编著的《真理与革命: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基本问题研究》(Wahrheit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r Grundproblematik der Marx’schen Gesellschaftskritik, 2020)、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编著的《鲍里斯·N. 尼古拉耶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产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溯源(1922—1940)》(Boris I. Nikolaevskij. Auf den Spuren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und der Archive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en (1922—1940), 2021)。
2020)、马提亚·伯伦德(Matthias Bohlender)编著的《真理与革命: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基本问题研究》(Wahrheit und Revolution Studien zur Grundproblematik der Marx’schen Gesellschaftskritik, 2020)、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编著的《鲍里斯·N. 尼古拉耶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产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溯源(1922—1940)》(Boris I. Nikolaevskij. Auf den Spuren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 und der Archive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en (1922—1940), 2021)。
这些正在开展的争论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争论。2017年MEGA2版《形态》出版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17—2018)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形态》的最新研究文章。格哈尔特·胡布曼(Gerald Hubmann)认为,虽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对《形态》的经典解读倾向于将其筹划为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打算出版这部手稿。该手稿的无序状态正是人们多次尝试提供新版《形态》的原因。胡布曼认为“不存在《形态》这部著作”。这一观点针对的是前MEGA2版《形态》的编者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因为陶伯特认为《形态》不是一堆不同的手稿,而是从属于同一部著作的组成部分。根据胡布曼的说法,《形态》并不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相反,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出版的一份期刊的组成部分,其中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赫斯不是《形态》的撰稿人,而是筹划中的期刊的撰稿人。胡布曼(以及U. 帕格尔和丹尼尔·德莱夫斯基(Daniel Drewski)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人物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麦克斯·施蒂纳。正是这种对峙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在费尔巴哈身上。这也是U. 帕格尔在他最近关于施蒂纳的著作(2020)中提出的观点。帕格尔试图改变过去研究中施蒂纳被边缘化的状态,恢复施蒂纳对《形态》的重要性。另外,他还全面梳理并比较了12个不同版本《形态》中“费尔巴哈章”的手稿顺序。马提亚·伯伦德在《真理与革命》中延续了帕格尔的理路,试图完全再现马克思与施蒂纳的联系,并特别关注了赫斯对施蒂纳的反驳。克里斯汀·韦克韦特(Christine Weckwerth)全面重构了《形态》的写作过程及其政治哲学语境,并特别关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真正的社会主义”视作意识形态的观点。宽特探讨了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和丹尼尔·布兰克(Daniel Blank)编辑的英文版“费尔巴哈章”。他认为,卡弗版“费尔巴哈章”试图将关于《形态》的解读再政治化,但其工作在政治上是非常狭隘的。该版本倾向于一种纯粹诠释学的解读,而没有实质考察不同版本《形态》中特定的具体的编辑实践。最近,卢卡斯·鲁道夫(Lucas Rudolph)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形态》的主要目标不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批评当代德国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二,关于马克思在写作《形态》前后展开的社会批判所蕴含的政治观念的争论,亦即关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争论。这场争论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观,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批判”的描述:“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观的争论起源于奥斯纳布吕克大学马克思学者的研究项目,他们将1843年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立场看作重新解读1840—1850年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功能演变的主导线索。无论是《神圣家族》中“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还是1850年代初的“批判的共产主义”,抑或18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伯伦德、舍恩费尔德(Sch?觟nfelder)和斯佩克(Spekker)认为,马克思的批判观需要从孤立的文本脚注解读方式转变过来,将其重构为一种有助于重塑19世纪政治斗争的社会对抗的产物。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这场关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争论发生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集刊新丛》(2016—2017)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展开的圆桌讨论,核心问题包括丹加·维莱西斯(Danga Vileisi)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早期共产主义之功利主义观的关系问题;扬·霍夫(Jan Hoff)和迈克尔·布里(Michael Brie)提出的马克思对19世纪20年代的反资本主义作家如罗伯特·欧文、托马斯·斯宾塞、约翰·格雷和托马斯·霍吉斯金的接受问题;纳迪亚·拉科维茨(Nadja Rakowitz)提出的马克思对蒲鲁东关于当代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批判问题,以及贝特尔·尼加德(Bertel Nygaard)提出的马克思在早期工人阶级运动中同共产主义政治家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的关系问题。
第三,关于MEGA1的历史的争论。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集刊新丛》第六卷中关于MEGA1研究者和大卫·梁赞诺夫在欧洲的确证者鲍里斯·N. 尼古拉耶夫斯基的研究专辑集中体现了争论各方观点。罗尔夫·黑克尔和瓦迪斯瓦夫·赫德勒(Wladislaw Hedeler)完整考察了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俄国革命前后的生活。1922年,尼古拉耶夫斯基因在苏联从事孟什维克活动而被迫流亡德国。但两年后,他被梁赞诺夫指派协调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沟通,并协助该研究所整理文件、档案和搜集资料。由于莫斯科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反孟什维克清洗运动和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尼古拉耶夫斯基于1933年离开柏林前往巴黎,1940年又移民美国。该卷的其他文章考察了尼古拉耶夫斯基进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过程,并追溯了他在建立研究所档案重要部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文献遗产)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该卷的最后一部分专门介绍了尼古拉耶夫斯基同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汉斯·施泰因(Hans Stein)、V. V. 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i) 和N. W.波塞摩斯(N. W. Posthumus)等苏联、荷兰与德国的档案管理员和编辑的通信。
第四,由对MEGA2第四部分中马克思笔记的特别关注所引发的关于马克思在1850—1860年代的经济理论的争论。这一研究趋势可概括为(但不限于)对马克思的《伦敦笔记》和《危机笔记》的研究兴趣。虽然许多马克思学者特别关注马克思《大纲》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但“亚细亚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住田宗一郎(Soichiro Sumida)基于《伦敦笔记》(尤其是第九笔记本)和《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亚细亚形式的观点,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诺曼·雅各布(Norman Jakob)试图从更广义的角度阐明马克思在1844年中期出版《政治和国民经济批判》一书的意图以及该计划直到1851年的发展情况。此外,他还考察了马克思寻找出版商的尝试以及他与罗兰·丹尼尔斯及恩格斯在同德国出版商科塔达成交易时的通信,以及马克思在1850年代初期如何继续他的经济研究。对于马克思《危机笔记》的研究,森贤治(Kenji Mori)和罗尔夫·黑克尔的文章尤其值得关注。森贤治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笔记》既是他研究1857年经济危机的产物,也是他系统收集整理《经济学人》《泰晤士报》《晨星报》和《卫报》等刊物中刊登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评论的结果。森贤治指出,虽然经济危机在19世纪并不罕见,但1857年危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是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也是适用于商业周期的经济模型的第一个成熟案例。1857年危机发生之前,马克思在185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下一次危机将与1847年危机不同,它将具有工业性质,而不是货币或商业性质。他还预见到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产品市场供应不足的双重危机。基于《危机笔记》,森贤治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是如何发展这一思想的。黑克尔概述了马克思对1857年危机及其在欧洲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危机对政治革命的潜在影响感兴趣的更广阔政治历史背景。黑克尔认为,马克思在《危机笔记》中进行详细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利用1857年全球危机这一特殊事例在经验上验证他的经济危机理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