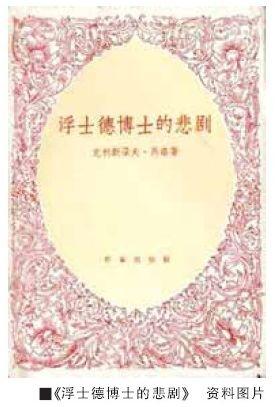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于1588年创作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该剧主角浮士德向梅菲斯特(Mephistophilis)提出的要求,大半是关于知识的愿望:解释行星运行的书籍、阐释植物药草的书籍、辩论占星术与天体学说、考察世界地图的准确性、参观昔日罗马帝国的城市构造。浮士德作为文艺复兴典型的知识人,被认为是马洛塑造的最具自传色彩的戏剧人物。马洛作为学者型剧作家,其戏剧充分体现了新科学对戏剧创作的革新力量,也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艺术在戏剧中的结合。
新科学及书本文化的流行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新科学的变革潮流影响了英国的科学思维与人文理念。一大批掌握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试图基于数学和科技领域的新成果,调整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中占据主导的亚里士多德学说。
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作为与马洛同一时代的研究者,立意重新考察自然,创建新哲学。他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有趣的是,培根曾以文学游记的形式,创作了《新大西岛》一书,其中描写了所罗门院这一科学研究机构,创建了自己心目中科学研究的乌托邦王国。
马洛也同培根一样,是接受近代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他被学者戴维·里格斯(David Riggs)誉为“英国自乔叟以来最会用诗意语言表达科学思想的诗人”。马洛于1581—1587年在剑桥大学接受了7年人文教育,获得了独特的文献资源。从马洛的戏剧中可以发现:新科学对于16世纪英国戏剧创作影响颇深。科学思想与戏剧的融合,不仅与天文、气象、地理知识的更新有关,而且与书本文化的流行相关联。
一方面,近代科学研究者开始认为天文气象不是神的干预,而仅仅是自然条件造成的大气环境变化,并逐步接触到日心说的概念。例如,罗伯特·瑞德(Robert Recorde)于1556年出版的《知识的城堡》中已经提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托马斯·狄格思(Thomas Digges)在1576年出版的《天体轨迹的完整记述》中发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部分翻译。另一方面,制图学的发展和地图册的出版构建了一个具有新科学思维的广阔世界。亚伯拉罕·奥特琉斯(Abraham Ortelius)于1570年出版的名为《寰宇大观》的世界地图册,被证实是马洛戏剧中地理想象的主要来源。
人文科学的发展还掀起了欧洲的“新学识”浪潮。书籍作为表现思想文化的工具与尺度,充分体现在文学创作中。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大学才子派”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出对书本典籍的迷恋。
新科学对戏剧空间的拓展
戏剧空间不只是纯粹的外在物质场所,也是戏剧人物理解世界秩序的观念模式。在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新科学对于想象空间和人物行动模式的改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天文探索从超验性信仰转变为实用性科学,关于天体的认知不再与古代神祇的宗教意涵相对应;其二,宇宙秩序观念的变动造就出以人类为中心人物的戏剧创作模式;其三,地理探索与殖民扩张,使戏剧主题呈现出殖民性的世俗欲望。
首先,天文术语频繁地出现在马洛戏剧中,如“巨蟹座的炽烈的热带中部”“摩羯座星位之下的亚马孙流域”“猎户星座似细雨洒落的景象”,以及“燃烧的彗星”“行星”“毕宿星团”“恒星”“流星”等词汇,展现了马洛在剑桥大学可能接受过的天文教育。另外,马洛还在戏剧第七场设置了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之间长达34行的对话,他们讨论天体知识,如月亮之外还有多少天体、天体是否都是球体等问题。虽然这些冗长的探讨很容易造成戏剧节奏的失衡,但也进一步说明了剧作家对于天文知识的痴迷,或展现渊博才学的写作欲求。
其次,星际间广阔的宇宙想象塑造出近代人物特有的宇宙性的英雄品格。“宇宙性”这一术语出现在苏联理论家巴赫金所著的《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主要指人类成为宇宙探索的重要依托,其力量可以改变宇宙元素的运行。浮士德的行动就包含着宇宙性的想象,他试图操控两极间运行的万物、掌握宇宙元素、成为天界的主神。而在马洛另一部戏剧《帖木儿大帝》中,帖木儿则宣称要“把炮口指向云霄,打破天堂的架构,捣毁太阳的金殿,敲碎全部的星空”。他甚至指称自己为三重世界的皇帝。这些包含人类伟大精神的宇宙性想象,都表现了新科学带给人类的精神指引。
最后,地理探索和地图学的发展,使戏剧中的地理坐标转变成满足欲望的抽象文化象征,而地理大发现掀起的殖民浪潮也影响了戏剧创作的想象范畴。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出现了“新大陆”“印度”“新近发现的群岛”等殖民性质的地理意象。
新科学与人文危机
新科学对于戏剧创作的变革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展现了科学成果与人文理念在戏剧中的结合;另一方面,知识增进了人类的自主性,从而引发了近代社会中知识与神学信仰间的矛盾。
学科的重新划分、地理的发现、天文的探索等都冲击了神学在知识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以学科划分为例,培根在《学术的推进》中将人类知识分为两类:神灵启赋的知识和人类靠官能所获得的知识。他模仿《马太福音》中“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话语,写出“属于信仰的,归给信仰”,试图将神学与科学彻底分离。
我国学者对浮士德主题的关注由来已久。马洛戏剧作品中被最早译介的就是1956年由戴镏龄译出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关于浮士德的毁灭,学者杨周翰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指出:其暗含着人文理想在16世纪后期遇到了宗教性压迫,也暴露了它自身的软弱性。近十年,邓亚雄、冯伟等研究者都先后以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为例,探讨文艺复兴知识分子在博学与宗教虔敬之间的两难处境。
进入20世纪,戏剧领域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新科学”故事的创作仍在继续。以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哲理剧《伽利略传》为例,该剧取材于伽利略(1564—1642)的生平史实,展现了伽利略因证实哥白尼日心说而遭受天主教残酷迫害的一生,同时也反思了科学成果与人类社会关系的问题。
科学知识改变着自然与人类社会,戏剧作为公共性的艺术形式,也不断沿着科学路径,探索着世界的种种可能性。戏剧中对于知识的探讨从不缺乏。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智慧所表明的反自然特性,到文艺复兴时代《哈姆雷特》中展现的知识与行动间的悖论,再到20世纪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贬斥的苏格拉底的知识,戏剧始终观照着人类的精神境遇。而马洛所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则写照了“文艺复兴人”在新科学所引发的精神启迪和信仰危机间的挣扎与进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