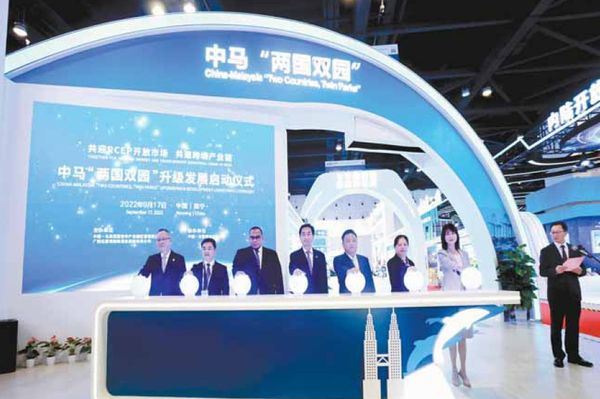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堪称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颇具本土原创色彩的史学理论,由此引发的“古史辨”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革新。但自“层累”说提出以来,学界的批评之声也从未中断。合理的批评有助于学术健康发展,但如果批评视角不断转换,且彼此之间存在冲突,那我们就有必要反思这些批评本身的合理性。近百年来,学界围绕顾颉刚古史考辨出现的诸多批评就存在这样的特点。
第一,学界批评的转变。学界对顾颉刚古史考辨批评的转变,在以下两方面有较明显体现:一是关于“破坏”与“建设”问题;一是关于“抹杀”古史问题。
首先,关于“破坏”与“建设”问题。1923年,顾颉刚论述旧有古史记载中存在着“层累”造成现象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经发表,便在学界激起了巨大波澜。当时,盛赞他“替中国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者有之,批评他“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者亦有之,且彼此之间迅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立态势。不过,就当时而言,无论说顾颉刚疑古过激、方法谬误,还是说他有损世道人心,大体都没有离开“打破”旧有古史系统的问题,即旧有古史系统到底应不应该“打破”以及如何“打破”等。而且,除去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苛责外,即便是偏于保守的刘掞藜、胡堇人等,也不反对怀疑古史,只是对于怀疑的尺度,彼此各有不同。
1930年前后,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批评顾颉刚不懂考古,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声音日渐增多。如卫聚贤就说,顾颉刚“闹来闹去,没有什么结果”,“这是他不知考古之故”。同时,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兴起,特别是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也为古史重建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视角,于是,批评顾颉刚不懂社会科学,不能见古代社会真相的声音又日渐增多。如李季、杜畏之等就说他对古史研究“没有入过门”,“最多不过砍破地皮而已”。可见,1930年前后学界对顾颉刚的批评,从“古史辨”初起之时的“打破”旧古史,转到了不能“建设”新古史方面。诚然,这些“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事实,但它们是不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则值得思考。否则,若中国古史研究每有进展,我们都回过头去批评顾颉刚“不能”,那这种批评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值得反思。
其次,关于“抹杀”古史问题。自“层累”说提出以来,就有学者批评顾颉刚“抹杀”古史、怀疑“历史本身”。如李济就有“中国的革新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的记载全都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身”的说法。近些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流行,又有学者提出,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相比,顾颉刚并没有否定“历史本身”,而是将旧有古史的层层伪作及其构造过程,全都当作垃圾废物甩掉不要。那么,顾颉刚的古史考辨到底在考辨什么?如果他将“历史本身”和相关记载,以及层层伪作的构造过程全都怀疑、抹杀、甩掉不要,那他强调的“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还有什么“流变”可“穷”?我们不是说上述观点全无道理,更不是说顾颉刚的古史考辨不可批评,但如果各种批评之间本就存在着冲突,那我们就有必要思考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核心旨趣是什么,这些批评是否对顾颉刚的观念有所误解。
第二,考辨“古史观念的演变”。学界讨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征引较多的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说的“三个意思”和《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的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打破”。不过,“层累”说的“三个意思”主要属于现象的描述,即描述了有关中国古史的记载中存在着一种“层累”现象;而四个“打破”则主要属于立场的表达,即主张想要辨明古史,必须“打破”四种陈陈相因的旧观念。它们其实都没有准确地反映出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旨趣。顾颉刚的旨趣既不是要“抹杀”古史材料,也不是怀疑上古历史本身的存在,而是要解释旧有古史系统如何被古人层层构建而成,针对的是有关上古历史的种种学说和观念。
顾颉刚对自己考辨的对象是旧有古史观念,始终都有明确的自觉。在提出“层累”说之初,他就说过:“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这里被他看重的“传说的经历”“史事的变迁”,显然就是指古史观念的演变。随后,他在论述四个“打破”时也强调,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集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由此亦可见,“层累”说针对的就是有关古史的学说和观念,而非客观历史。事实上,客观历史本身也无法“层累”。
第三,“解释‘古史’的构成”。顾颉刚考辨古史观念的演变,不只是要厘清其出现的时代序列,其核心旨趣在于“解释‘古史’的构成”。这一点,在1924年《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中已经表露出来。这份计划的前四个学程旨在厘定各种古史料、古史说出现的时代序列,顾颉刚称之为“形式上的整理”;第五个学程借助民俗学的知识“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才被他视为“研究古史的内部”。到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中,顾颉刚说得更为明确:“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
可见,顾颉刚的古史考辨更偏重于历史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层面,其研究兴趣在于前人对上古历史认识的演变,亦即世代相传的古史系统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上古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对此,确如论者所说,顾颉刚这种旨趣和后现代史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我们也需注意,顾颉刚关注的重点不是上古历史真相,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真相的追求,更不意味着他否认了真相的存在。
第四,史料的“移置”。考辨古史学说、古史观念的演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辨伪问题,但顾颉刚的辨伪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去伪”,而是将这些史料“移置”到它们出现的时代,作为研究相应时代思想观念的材料。顾颉刚自述,许多伪材料,置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破坏它,并不是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就顾颉刚的具体研究而言,某些出于战国秦汉的古史说相对于上古历史固然是伪史,但它们确实是战国秦汉间人对上古史的认知或观念,而顾颉刚所考辨的正是这些认知、观念的演变过程。这也是他将自己定位为“‘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的原因。
自“层累”说提出至今,始终有学者以伪书中也有真材料为由,批评顾颉刚抹杀古史、抹杀史料、抹杀传说。事实上,批评者与顾颉刚的不同,并不是伪书有没有“真”材料的问题,而是他们所追求的本就不是相同的“真”:批评者追求的“真”指向上古历史,顾颉刚追求的“真”则指向“伪史”产生的时代;批评者是要在传世文献中找寻上古历史真相,顾颉刚则是要借“伪史”窥测其产生时代的思想观念,以分析旧有古史系统是如何被建构而成的。这种不同反映的是学术观念的差异,正如顾颉刚回应柳诒徵的批评时所说,“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
综上所述,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核心旨趣是“解释‘古史’的构成”,即解释旧有中国古史学说、古史观念是如何被后人特别是战国秦汉间人因应“时势”需要逐步构建而成,揭示其中有不少说法其实是后世史实投射到上古观念的结果。上古历史真相和古史材料真伪在顾颉刚的古史考辨中虽都无法缺席,但二者都不是他的最终诉求,他的诉求乃是通过上古“伪史”透视中古“真史”。这一点,实际已经超脱了静态的真伪之辨。顾颉刚这种史学观念在今天或许并不新奇,但在百年之前,确有超迈时贤甚至“不可理解”之处。而这也正是顾颉刚在考辨古史的同时不断进行自辨,反复向学界澄清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不是什么,而学界似乎又有些置若罔闻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