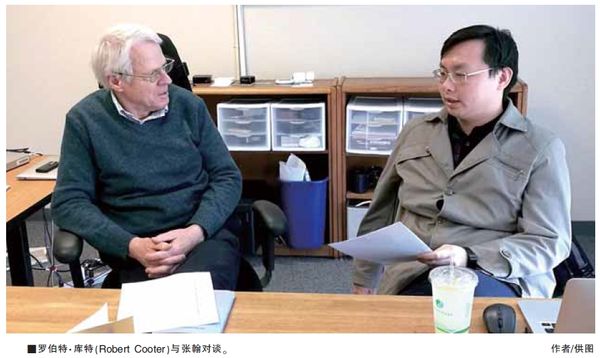
以下关于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学的对话,根据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张瀚的系列法律经济学对话编辑节选而来。对话发起人张瀚是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库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奖得主。
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信息机制不同
张瀚: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与法律的历史有关,正如我们此前提到的,在普通法系和成文法系中,法律人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方式是不同的。大陆法系主要是基于成文法这样的法律渊源,而普通法系主要是通过判例来传递知识,有时候也通过成文法。这是将法律渊源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两种主要方式。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您认为哪一种效率更高?
库特:我认为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制度性记忆”。在人类制度建构中,有很多知识或事物是个人所没有的,但存在于制度中,这是人类制度重要的特点。比如,假设美国除宪法外的法律文件全被毁掉,那便需要人们花上数十年才能搞清楚美国政府的运行机制,而且会使得宪法成为不知如何实施的空洞草图。如果想搞清楚宪法原则的具体含义,需要经过多年的管理实践。
有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当一切事情都被记录成文以后,就将制度保存下来了,但其实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制度的含义。制度是包含了隐性规则的,我们不得不被这种隐性规则同化,不得不融入这种隐性规则。还有一个例子,在阅读民法典时人们会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在某些领域的规则是一样的。日本对德国民法典进行了翻译和部分修改,然后为己所用,但和德国的法律适用结果却可能完全不同。假如遇到同一个侵权案件,日本的法庭和德国的法庭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即使他们援引的规则是相通的原则性规定。
张瀚:这里面可能存在着特定文化背景下对法律渊源解释的差异以及法官本身成长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例如,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规定,在不同国家(即使同属一个法系)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案件法律适用结果的差异。
关系契约与完备合同
库特:我认为,法律是一种受文化影响的制度,而且不是所有法律制度受文化影响的结果都是好的。日本法律制度受文化的影响很大。有些人认为日本人本质上不是热衷诉讼的人,但其实人们不热衷于诉讼的原因有很多。所以,如果您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也许不太会考虑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张瀚:是的,我曾经阅读过一些材料,以索尼公司为例,其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在尝试开拓美国市场的时候,便感到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很大差别。他发现美国的律师很多,人们希望确保合同载明所有事项。但是在日本,虽然也有条款或者合同,却未必会具体到每个细节。
库特:我想和您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是阿科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我的。这位高管所在的阿科石油公司是一家美国企业,当时在为开发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进行短期合营,其合作伙伴是一家日本企业。而日本人和美国人对彼此合作并不熟悉,对双方而言这种合作都是一件新鲜事。所以,他们在酒店租了房间,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谈判。在谈判将要结束时,美方律师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显然这是一份合作合同,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订立合同成功合作。但日方代表看到后立刻离开,并终止了这次交易。因为日本人对合同的概念是建立一段关系,而美国人认为合同是制定一些约束双方的规则。最后,他们没能达成合作,因为他们无法让这两种理念相融,无法达成一致。
张瀚:我们都知道在制度经济学里有“关系契约”的概念,理想的合同理论中则存在“完备合同”的概念。您所讲的上述例子中,美国企业似乎更注重订立书面合同,如果有可能甚至倾向于订立一份完备的合同,试图把谈判过程中确立的细节尽量在合同约定中完全、彻底地固定下来,以便未来作为双方的行为指引。而日本企业在这个案例中的思路似乎更接近关系契约,漫长的谈判固然是为了达成共识,但更是为了确立一种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中既包含对合作总体框架和大体共识的确认,又包括对双方未来在关系契约中进一步确认或变更合作细节的灵活预期。关系契约和完备合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经济学合作思路,在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库特:当然有,关系契约的特征包含承诺的标准,让人知道这段关系不会突然或迅速结束,而且关系契约中的每一方都有很多种方式来惩罚对方。由于每一方都有很多惩罚对方的方式,所以将它们全部写下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一直喜欢以我和我母亲周日共享晚餐为例。如果我母亲邀请我周日一起吃晚餐,我许诺会在晚上六点到,但直到八点才到。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存在承诺,她有很多种方式惩罚我,即使我们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合同关系。这就是关系契约的运行方式。这是一个通用的框架、一种普适性的理解,所有细节都从互动中产生。合同是用来制定规则,而不是建立关系的,它只是尽可能明确地写下谁具体要做什么。
张瀚:我想这也许和我们此前的讨论有一些关联。关于完备合同,存在一个平衡问题:一方面,越完备的合同,起草成本就越高,但另一方面,事前约定的明确性会降低其执行成本。因此“合同的事前约定成本+合同的事后执行成本”的总和最小化,是完备合同理论(类似于物理无摩擦的理想状态)逻辑推演后的最重要的实际应用。当然,在东亚和中东,人们传统上倾向于合同是关系契约,会随着原则和信任发展,如果发生新问题则进行再次协商、相互惩罚和决定退出。退出也算是广义的惩罚手段之一。
关系契约与师徒传承
库特:我以我们此前提到的文化为例,当你旅行的时候这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两年前,我在日本的校友会作了一次演讲,校友会位于东京,是为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的日本校友设立的。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们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这是他们入学时就形成的关系,而且他们不会忘记。我非常欣赏,同时也非常敬佩这一点。我认为在美国,我们很少对母校投入感情,虽然我们向母校捐赠,但我不认为我们拥有他们那种责任感。
张瀚:我认为不只是日本,其实这也是东西方的差异。我举一个例子,一般研究生会有一名导师。在东方国家,他们之间更像是一种长期的终身智力支持和社会性契约关系,但在美国这更像是一个传统合同。
库特:我认为您说的非常对。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确定日本人是不是比韩国人或者中国人更重视关系,你有这种感觉吗?您认为在中国、韩国或者越南,对关系的重视程度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在整个亚洲文化区域内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您认为日本人尤其看重关系?
张瀚:我不太清楚越南和韩国是怎么样的,但是在中国,我认为学生与导师之间的联系是很强的,方式也比欧美传统。即使毕业后,很多学生也会与导师保持一种长期关系。在我们的传统里,即使是只教过自己一天的老师,学生也会在道义上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历史上甚至存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尽管现代观念上出现了改变,但历史的影响很难完全消除。
库特:这非常好。我带的很多研究生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和研究生合作写过很多论文,我们的关系确实与父子或父女关系类似。因为当我和研究生建立关系之后,我觉得我应该照看他们的事业,应该关心他们是否得到提拔、为什么得到提拔以及他们是否遇到困难。我认为上了年纪时仍能和学生保持这样的联系,会让人有满足感。
张瀚:作为老师确实会关心学生的发展和事业,这是非常正常的。
制度性知识有不同的具体面向
库特:回到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区别,成文法的规则与普通法是不同的,制度也不一样。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相反。不仅仅是侵权责任规则不同,法院的组织方式也不同,去法院起诉的人也有不同的法学教育背景。因此,有关美国法院和法国法院的知识存在着一些实质性差异,这些知识被称为制度性知识,它们的具体面向不同。
认为制度能被简化为成文法的想法是错误的。正如日本可以引进德国民法典的规则,但实际保持着自身特色,它的实践可以说是完全日本化的。毫无疑问,这是日本的制度,而不是德国的制度。日本人对此从未怀疑过。日本人知道他们不需要德国民法典,他们想要的是使德国民法典日本化。所以即使条文在写下来时相同,但制度还是不一样。制度运行的记忆代代相传,随之产生了独立的文化。
张瀚:我认为因为这是对法律的解释和理解,而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或者规范的解释。我这里指的解释方式是广义的,不局限于法官的解释,也包含民众的理解。在法院,法官需要解释法律,需要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进行解释,司法实践中也需要解释。即使我们不谈律师、法官或者教授、专家的理解,只是对于普通人,对于同一个法律原则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例如,诚信原则、平等原则在任何一个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都很常见,不同国家的每一个个人,当他们说到诚信原则、平等原则,都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就像您之前提到的,这些无数个体的理解也会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成文或判例的形式仅仅是制度性知识的表面载体。例如,您说的“黑体字法”(black letter law)和我们说的成文法,即使它们在写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差不多,但其实践是不同的。
库特:我举一个例子,在禁止单方交流原则诉讼中,法官掌握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在庭审中获得和审查,不能来自任何其他渠道。我身上曾真实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我第一次在法庭上提供专家证词时,不知道这些规则,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我的作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午餐时间到了,法官宣布休庭。我当时比较疲惫,在走出法庭去坐电梯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在法官之前上了电梯,这就意味着法官不能坐同一趟电梯。
张瀚:您作为专家证人,不应和法官处在同一个空间,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库特:是的,我不能和法官坐同一趟电梯,所以电梯载着我下去了,而他不得不继续等待,这真的是太蠢了。禁止单方交流原则具体起作用的方式因地而异。比如,在德国的法院,有时法官会过来和教授吃午饭,讨论某个案件中的法律原则,而不是讨论案件事实本身。我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现在不会和教授讨论在审案件的法律原则,起码不是所有正在审理的案件,虽然对此我不是完全确定。一个来自南美洲国家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那里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当你被牵涉进某个案件中,成为原告或者被告,又得知了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是谁,你会尝试去找一位曾和法官在法学院一起上学的律师,这个律师就会去和法官喝咖啡,讨论案情。
张瀚:我感觉这有点像腐败或不正当地影响法官。
库特:可能是的。和我交谈的这个人说,这种行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从一个角度看,这是腐败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做是有效率的,因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法官能弄明白很多事情。
张瀚:如果规则设定为不允许去咖啡厅这种地方私下会见,但还是可以保留一些正式的信息传达渠道。比如,直接通过办公电话沟通,不是法官的手机,而是法院办公室的电话;也可以通过法官助理进行正式程序上的间接沟通。
库特:我认为这些制度取决于设立的方式,这些事情一直在变化。例如,美国总统是需要保存所有办公室来访记录的,人们可以从中得知他曾经和谁谈过话,这是一项新规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私法适用中再分配问题的法律经济学研究”(22BFX1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黎宇乔等对翻译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