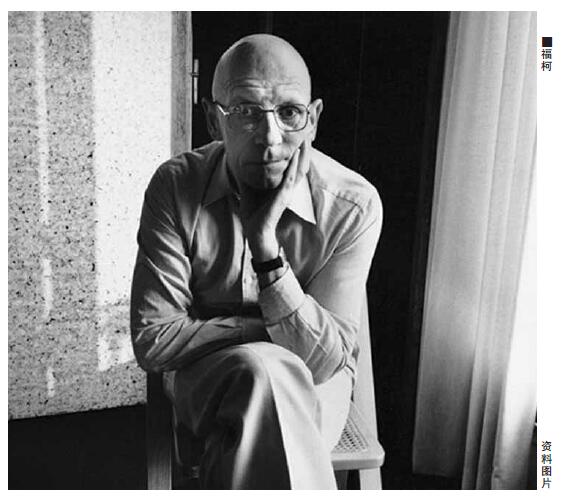
福柯对真理的思考与他对“人的历史本体论”的研究紧密相关,是他立足于现代人的当下生存境遇对古老的苏格拉底之问的审慎回答。从对传统真理观的不信任、对“知识—权力”的谱系学批判,到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真”之内涵的考古、对“说真话”伦理实践的重新阐释,福柯对待真理的态度经历了由解构到构建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福柯尝试揭露由启蒙传统“真理观”所维系的现代社会真理制度对人愈发匿名、严苛的治理。同时,他也在其后期思想中积极重建“真理”范畴的伦理向度,探寻抵制治理、重拾“人之自由”的可能路径,此即他对“说真话”的探索。这一探索为现代人提供了走出“当下生存困境”“人该如何生活”的一种选择、一个苏格拉底之问的福柯式回答。
现代人对“真理”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笛卡尔开启的认识论转向。这种真理观认为真理根植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以不证自明的基础信念(我思)为基点,通过理性推导使“我思”之上的非基础性信念得到确证,从而构建起真理知识体系。此外,这种真理观极具启蒙色彩,它主张真理应该与权力无涉,真理是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哲学家们常赋予这一真理观高贵的出身,即它起源于柏拉图哲学,中经中世纪,达至现代,以“认识你自己”
 这句古老的德尔菲神谕为线索,建立起连续、普遍的历史。
这句古老的德尔菲神谕为线索,建立起连续、普遍的历史。
福柯对此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一方面,他认为笛卡尔以降的真理观将真理局限在“认知、知识(connaissance)范围内”是偏颇的,福柯不认同现代人获取真理的认识论途径,认为认识本身成为通向真理的途径既是真理史现代时期的开始,也是真之伦理向度被遗忘的起点。在古代,人们必须付出禁欲、苦修等实在的主体代价,即通过“精神性”(spirituality)地锻造自身,而非一次简单的认识行为,才能达至真理。另一方面,福柯也反对认知真理标榜的客观中立,因为它的出身并不像启蒙思想家所赞扬的那样光明与崇高。相反,它的出现充满了居心叵测和诡谲多疑。它不是帮助我们摆脱权力斗争、获得自由的东西。相反,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而权力的运转需要不断地制造真理。福柯早期对疯癫、罪犯、人口的研究其实是在描述现代社会“真理生产”的治理历史,这种“真理生产”得以持存的前提是现代人处理主体与真理关系时所使用的“解释学”方法,是求真欲望的永不满足。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考察了“区分权力”(pision)如何催生出“精神病学”作为自身运转的合法性依据、“精神病学”又是怎样借助权力将“疯癫”确立为认知对象的历史。他意在揭露“精神病学”如何假借真理的名义确立起“正常”的标准,并以此来排斥、裁决原本处于权力边缘地带的“疯癫”群体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犯罪学”如何助力“规训权力”顺理成章地植入惩罚体系,“纪律”又是怎样为“犯罪学”锚定了在“罪犯”肉体上的作用点的过程。为了更深入地支配社会,宏大的王权往往力不从心,而规训权力则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抓取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弥补王权无法触及之处,即把控犯人所有的细节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了解他的表现、精神状况、道德态度等。而这些正是“犯罪学”的“知识”,规训权力与犯罪学的勾结造就了驯顺的肉体。福柯旨在说明刑罚制度的改革并非人道的,相反它是暴力的,知识—权力加强了对罪犯的控制。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探讨了“生命权力”与“人口学”如何相互配合,实现了对“活人的征服”,造就了西方“自由与民主”社会假象的历史。为了实现对群体的控制,权力将自己塑造成“扶植生命”的生命权力,通过预测、调整大众的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再生产比率等“生理常数”来实现总体的平衡和稳定。福柯批判现代人将“人口学”等科学奉为新的宗教这一荒谬做法,同时揭露了这种真理默许的“增殖和杀戮”的残忍逻辑悖论。
如果我们将上述学科的产生时间大致作一统计,就会发现它们均出现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左右,即福柯所说的“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的诞生时期,这绝非巧合。这是因为此时笛卡尔式的处理真理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解释学”方法成了人们获得真理的基本逻辑,“大声而清楚地说出关于自己的真相”的这种自白(confession)成为人们制造关于自身真相的主要方式,人成了科学视域中有待被解读、破译的客观对象,权力要从他的身上逼迫出“真相”。这些所谓的真理与特定技术相互勾结,成为人类了解自身的工具。知识—权力借力激昂的“求知意志”,遵循着“越知越安全,越知越确定”的治理逻辑,一路高歌猛进,将所有人收割为支配对象。与其说这些学科的出现是知识的进步,不如说是出于维护社会治安,以权力关系对人进行愈发严密的宰制。换句话说,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因为它的运转流畅需要有真理的润滑,权力不停地向我们提问、调查、记录,使对真理的探求不断制度化、职业化。更残忍的是,我们乐于接受这种真理游戏,知识—权力形成的真理制度构成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遵循。
然而,福柯通过词源学的考察,发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真”(Alêtheia)的内涵并不限于认识:“真”是不隐藏;“真”是一种本质,与影子相对;“真”是直、不弯曲;“真”是自我保持不变。总之,古人的“真”更多指涉人的行为、品行的伦理层面,是一种“力量性真理”。这种“真”追求的是“真理主体化”,即把具有真理性的话语内化、嵌入自我,成为在手的力量性真理指导实践,继而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完善品格,实现人的自我风格化审美过程。这正是福柯所说的“直言”亦即“说真话”(parrhêsia)的伦理实践。虽然呈现形式也是“真的逻各斯”,但是“说真话”是一种“知识的精神化”,需要实实在在地付出“工夫”(ascétique),目的是“关心自己”、实现自我的自由与审美。
福柯通过考证发现,古人的“说真话”实践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伦理塑造。一方面,它涉及人的自我伦理修养,即“净化方式”的说真话。这一实践要求人成为一个“诚言者”,以自身为目的,完成自我净化的程序,才能获取真理,即能够通过“听、说、读、写”四种工夫对从外部接收来的“真理”进行占有,使主体与真理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在此基础之上,还要通过“实际训练”“沉思”等修养实践将已占有的真理转化为自我的“品行”(êthos)。如此一来,自己就成为一个兼具真理与道德的主体。在古代只有伦理主体才配拥有真理,伦理主体与知识主体是合二为一的。“说真话”使真理成为一种“装备”(paraskeuê),用以对抗人们生活中遭遇的苦难,以便拥有德善和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关系到对他人的伦理责任,即“勇气方式”的说真话。这一实践要求人成为一个“敢于对他者诚言之人”,不怕牺牲、下决心来推动他人完成“真理的主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说真话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游戏”,这是因为“诚言者”要以直白、完整、明确的表达将自己掌握的真理传递给“聆听者”。这种传递不是单纯的真理表述,而是要以“真话”来改正、批评聆听者的错误,且批评是“向上”的,即“诚言者”甘愿冒着死亡的风险,自愿地选择对权威“说真话”,以帮助其实现对真理的占有与内化。“诚言者”在对他人“说真话”的实践中实现了对自己的伦理塑造,将自我打造为一件“美的作品”,同时也产生了利他的伦理效果。
通过对以上两个维度“说真话”实践的考察,福柯发现古人对待真理的态度有别于现代解释学的态度,并不引诱主体“坦白”内心的“真相”,追求对万物的认知,而是以“真理”的自由实践促成美好的品格。真理的作用是指导人们去拥有幸福和审美的生活,这是古人特有的生存美学路径。然而,这一哲学传统已经被求真意志主导的“知识—权力”制度彻底遗忘和掩盖了。福柯重构“真理的伦理向度”,给予现代人诊断、批判“知识—权力”宰制制度的一种全新视角——要以“说真话”实践将自我风格化为无限种可能,将自己打造为一件美的作品自在于世,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权力关系对人的“客体化”,接受既定的“身份”和“面孔”;要以“说真话”实践向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真理制度”发起挑战,将所谓客观中立的认知真理重新抛入怀疑和批判的空间,以抵制“知识—权力”对人不易被察觉却严密苛刻的支配。
从“知识—权力”到“说真话”的转变,与其说展现了福柯真理观的流变,不如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探索现代人摆脱生存困境、实现真正的自由之法。福柯为西方哲学找回了失落已久的真之伦理传统,以“说真话”实践来对抗“知识—权力”的过度治理,对“How is one to live?”这一古老的苏格拉底之问作出了独树一帜的回答。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