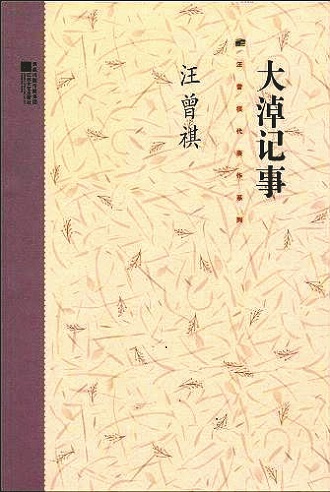
汪曾祺出生于水乡高邮,抗战期间,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自然山水的启悟、家乡文化氛围的熏陶、随遇而安的处事态度,使汪曾祺的思想底色上烙有深刻的禅宗印记。禅宗思想浸透到汪曾祺小说的主题意蕴和叙事艺术之中,也使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溢出明显的禅趣。
书写禅静随性的世俗生活
汪曾祺十分推崇苏轼诗中“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空静观。他认为“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汪曾祺《无事此静坐》)这种审美静观心理的养成一方面得益于庄子的“心斋”“坐忘”等美学主张,另一方面也潜隐着禅宗思想的影子。禅宗认为,审美观照,既不住有,也不住空,即空即有,非空非有,顿悟见性。心灵澄澈宁静,万象则历历分明。心空则万物自由鲜活,生机勃勃。宁静而不枯寂,空无而生万有。这种融合了佛道思想的禅静之心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心态。汪曾祺在创作构思时喜欢静坐,小说创作往往都是“心闲气静一挥”而成的。以这种禅静之心观照社会人生,书写凡俗生活,自然会使其作品具有浓厚的禅意。
汪曾祺小说所写的多是凡人俗事。他描绘三教九流的凡夫俗子,展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如《收字纸的老人》中的老白,孤身一人,挨家收字纸,虽粗茶淡饭,但也怡然自得。《钓鱼的医生》里的王淡人日常生活无非是诊病、送药、钓鱼,但他活得洒脱自在。《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平时生活悠闲自在,但在“炕蛋”期间,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即使在其代表作《受戒》中的和尚们,他们的生活也是世俗化的。汪曾祺笔下的这些人物不沉溺于生活的悲戚,安于日常当下,乐天知命,凭着一颗纯然之心,顺其自然地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禅的境界。
营造空明澄澈的小说意境
汪曾祺小说世界中人物的日常行住坐卧处处有禅,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情景交融、神与物游、虚实相生的特征,在小说中营造出了空明澄澈的禅宗意境。
《受戒》《大淖记事》《钓鱼的医生》和《鸡鸭名家》等小说无不意境淡远,禅意绵长。小说《大淖记事》开篇就是对大淖四季风景的描写。这里春天一片翠绿,夏天芦荻吐穗,秋天四野枯黄,冬天白雪覆盖。不同季节的风景变幻中回荡着自然的韵律。小说接着叙述了大淖周边的一幅幅风俗画。周边百姓的是非观念、道德标准与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里女人和男人的心情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即心里是否“情愿”。《大淖记事》描绘的风景、风俗和故事都贯穿着随缘任运、自由自在的禅意,从而呈现出澄明的意境。
在《钓鱼的医生》中,主人公王淡人有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去给被洪水围困的村民治病。即使对于这种急公好义的壮举,汪曾祺也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渲染,而是点到即止。王淡人竭尽全力为身无分文的汪炳治病,把他留在家里住,管吃、管喝。汪炳把王淡人留着配药的一块云土抽去了一半,把王淡人祖上传下来的麝香、冰片也用去了三分之一。妻子问王淡人:“你给汪炳用掉的麝香、冰片,值多少钱?”王淡人则笑着说:“没有多少钱。——我还有。”对于王淡人的这些行为,作者本可以将其写得慷慨感人,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处理,而是用平缓自如的笔调,凸显出他淡泊随缘而又不失坚韧的性格。这篇小说从多个角度表现了王淡人“一庭春雨,满架秋风”的淡然心态,同时也营造出一种悠远澄澈的意境。
追求随事延展的叙事结构
不同于情节曲折、结构严谨的传统小说,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结构随事延展,自由随意,灵活多样。他曾说,“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汪曾祺的这种艺术追求,依然渗透着禅宗“随缘任运”的精神。“随缘任运”在其小说叙事中的表现就是随事延展,为文无法,行云流水,不刻意为了文学成规而削足适履,也不会扭曲生活的常理。但在“随缘”中不随波逐流,也不固守成规;同时在“任运”中忠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本心。
《受戒》等小说的叙事结构脱离了传统小说起承转合的情节模式,也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冲突,而是信马由缰、娓娓道来。《受戒》叙述了荸荠庵里五个和尚的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但故事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作者只是将其连缀起来并置在小说中,叙事结构类似“画簿”。小说《岁寒三友》更像是国画“岁寒三友图”,“三友”相对独立,仅靠一股“寒气”将它们联系起来。小说里的三个人物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也各自上演着自己的故事,在作品中各占一块。朱光潜在评论京派作家废名的小说《桥》时,概括了这种“画簿”式结构的特点。他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它容易使人感觉到‘章与章之间无显然的联络贯串’。”汪曾祺作为京派代表人物之一,承其流风遗韵,小说叙事也倾向于采用这种“画簿”式结构。
汪曾祺的小说冲破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文体边界,形散而神聚,不合小说的一般规矩,而又亲切自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汪曾祺的小说情节淡化或无情节。其小说创作的这一特征与禅宗随缘任性、顺其自然的意趣有很大关联。
运用空灵隽永的诗化语言
禅宗不只影响了汪曾祺小说的主题意蕴和叙事结构,其小说语言也颇具禅趣。禅宗“顿悟见性”的直觉思维方式融入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创造过程。在禅宗看来,“顿悟”是见性成佛的唯一途径,不由阶渐,当下即成,超越知性,单凭直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越了知性逻辑,不涉理路,很多时候不采用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这种诗化的语言只是直观地描述眼前的景象,依靠直觉铺排词句,词与词、句与句并置而立,留下了大量“空白”,从而营造出空灵的意境。如果仔细品味,这些“空白”之处含有绵长的诗意,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元好问曾论及禅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他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答俊书记学诗》)此语也可以用来概括禅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关系。汪曾祺用小说的形式来书写禅意、营造禅境、呈现禅趣;同时,禅宗思想也让他的小说具有了空明澄澈的美学特征。二者交相辉映,使汪曾祺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 1 胡大雷:赠答——诗歌的叙事与社交功能
- 2 简讯
- 3 《以民意调查为武器》
- 4 跨界合作助推可持续发展
- 5 日本年轻人留学意愿偏低
- 6 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举办环境变化与野...
- 7 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发展
- 8 加大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力度
- 9 中俄合作迈入新时代
- 10 教育活动史研究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