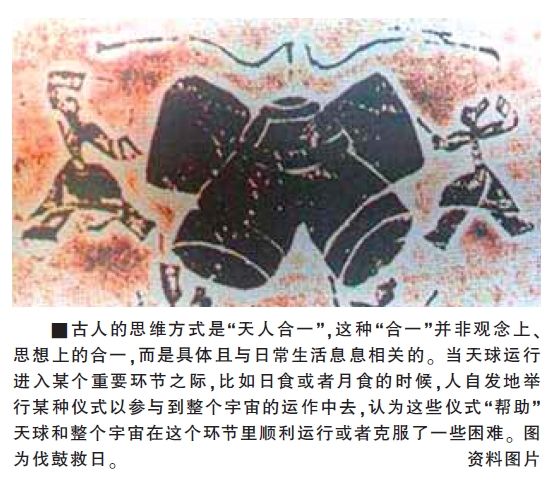
前阵子,甲辰龙年比癸卯兔年要少30天这件事在笔者所在的天文爱好者群里引发了一阵讨论,相关媒体也进行了相关科普。简单来说,正因为太阴历和太阳历分别以月球和太阳的运行周期为标准,所以在纪年的结果上当然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是月相变化的周期还是地球公转的周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整数,因此也总会产生一些对历法的“人工修正”。比如太阴历会设置“闰月”,太阳历会设置“闰年”。对于这样的人工修正现象,可以理解为对天球运行所造成的“时间剩余”的一种观念性补充。有人甚至认为,所谓的“补天神话”就是对这种时间补充的一种浪漫化表达。毕竟古人在解释何以出现岁差现象的时候,也用共工怒撞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来解释,而这也是传说中“女娲补天”的直接原因。
天文观测与古代宇宙论
岁差现象和历法中的置闰直接有关,这足以说明天文观测的复杂性,表明古人早就观测到天体运行数据偏差和数据剩余。即便天体运行周期本身并不是一个整数,但不妨碍古人认为它们是时间和宇宙秩序的表现,不仅“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且将之神圣化。倘若有人仔细看看《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封的所谓“正神”,就可以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星神。有的学者认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最古老的宗教是“拜星教”,即便在农业兴起、这种古老的宗教已经被所谓的“城邦宗教”取代之后,仍可以在各种宗教中找到它的影子。比如萨满教中极为典型的星神崇拜,以及在道教中普遍存在的对诸天星斗和“斗姆”的崇拜。而王莽直到败亡,仍指望自己仿照北斗七星做的特殊装置“威斗”,能够借助星辰之力镇压起义军。
我们常常说,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但在“轴心时代”的普遍哲学突破以前,这种“合一”并非一种观念上、思想上的合一,而是具体且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除了通过观测天象来制定历法以外,恰恰因为天象本身并不完美,所以整个天象乃至宇宙的完满运行,必须要有人的参与。这种参与除了观念上对天球运行产生的数据剩余进行补充外,更为重要的方面则在于当天球运行进入某个重要环节之际,人自发地举行某种仪式以参与到整个宇宙的运作中去,并认为这些仪式“帮助”了天球和整个宇宙在这个环节里顺利运行,或者克服了一些困难。而这样的环节,也就是“节日”,节日就是诸天运行的“节点”。在《尚书·尧典》中就已经出现了立春、立秋、春分和秋分四个重要的天球运行节点,这四个节点在后世也成了古代人的基本节日。
我们现在可以把古代这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一般性地理解为“宇宙论”(cosmology)。正如“宇宙”(cosmos)这个词的词源“化妆”“修饰”所透露的,它暗示了眼下这个有秩序的宇宙是一种对于原初无序的克服和镇压的产物,是秩序克服了混沌的结果。比如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里,世界的原初状态是“混沌如鸡子”。在这种世界图景中,不仅到了春分、秋分等能呈现天球运行重要位置的时刻,要以节日形式欢庆宇宙秩序的平稳,而且当异常天象如日食或者月食出现的时候,也要举行相关仪式。因为在这个时候,古人会认为原初被克服的无序仿佛挣脱了封印,正在威胁眼下的宇宙秩序,所以自己也要“出一把力”,帮助天球平稳运行,使宇宙重归秩序。比如《春秋繁露》就提出“日食……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通过“鸣鼓”和“朱丝”这样仿佛在“吓跑”日食的威胁仪式,人也就参与到了对天象秩序的恢复中,如此方能“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同样,在古埃及,人们通过尼罗河的水位和天狼星的位置来制定历法,等到了河水涨落的关键时节,法老王要亲自下河举行某种仪式,“帮助”尼罗河正常运行,进而“帮助”周天运转正常。
对于这种古代的天人关系,《易传·文言》总结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种“亲自参与”意义上的“合”,一方面体现出了神话—宇宙论时代人对于宇宙运行的高度参与意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某种人所认为的自身对于宇宙运行的“责任感”。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神话时代,眼下的世界图景也不再是古代的那种宇宙论,但节日的存在仍然是一种古老的记忆,一种“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本能的回响。
节日、记忆与剩余
当然,这种记忆也不总是伴随着美好和欢庆,它同样伴随着危机意识、杀戮和禁忌。正如前文所言,古人一方面担心原初的无序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从各种宗教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挖掘的证据中,我们也可以设想古人的另一种面对失序之际的“危机公关”方式,即宇宙的秩序和眼下的政治秩序,以及统治者的德性是合一的,如果这个政治秩序出现了危机,那么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法和“恢复”宇宙秩序就成了同一件事。而既然对于秩序而言,无序乃是一种本该被克服的“多余物”,那么献祭所谓的“剩余”就成了必要的。比如考古学家就向我们揭示,在玛雅帝国摇摇欲坠的晚期,向太阳神进行人祭的规模一再扩大。而《圣经·旧约》也表明,当犹太王国动荡的时候,不仅信奉异邦神的人数在增加,甚至出现了将儿女通过火祭献给所谓“摩洛”神的记载。正如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言,倘若神话仅仅是“迷信”和“人类思维的童年时代”,那么为什么古代人为了进行这些祭祀不惜血本?这无非说明了神话时代的宇宙论思维模式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英国著名希伯来学家斯宾塞(John Spencer)在他的名著《论希伯来人的礼法》中就论证过,近东地区普遍存在的割礼现象其实并非一个单纯的医学行为,而是一个宗教仪式,它意味着去除“自然人”身上的“剩余”,让人“文明”,进而与当下的世界秩序实现一致。所以也就如福柯所言,“文明”的确立也同时意味着“禁忌”“不文明”和“文明外剩余”的确立。
不过,正如盘古神话所表现的,原初的无序同时也是把后续一切都囊括在自身中的母体,尽管它被克服了,但一切原本就包含在其中。它既意味着万物的死寂,也意味着万物的沉睡和未来可能的苏醒,在许多神话中,原初无序的象征就是水和鱼。比如在半坡文化的出土文物中,著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被用作儿童的瓮棺的棺盖。这不由让人想起《山海经》里关于五帝之一的颛顼的那则著名神话:“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所以尽管对于当下的宇宙秩序而言,原初无序的“剩余”是有害且需要驱逐的,但它也代表着原初的无限可能性,代表着死与新生。英语“幸运”一词的词源乃是罗马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她也被称为“初生之福尔图娜”,在这个称呼里,“初生”和“福尔图娜”是同位语。这位女神不仅掌握着幸运,也掌握着冥府和轮回,她同时也代表着世界本身的无限丰饶。所以在这位罗马女神身上,原初无序之为剩余的形象也越发明显了,而她也恰恰告诉我们什么是幸运:幸运就是按道理来说本不该存在、但恰恰存在的东西,正如无序也是按道理来说不该存在的东西。
所以总的来说,尽管节日背后蕴含的神话—宇宙学世界图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对于它们的种种记忆仍以习俗和节庆的方式保留在我们的生活和伦常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斥为“封建迷信”,而是要明白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留下的记忆,是人类曾经走过的文明道路的路标。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或许中国文明更加乐观和积极,不害怕无序的“剩余”,而是要把它留下来,然后吃掉。毕竟“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庆仪式,或许我们的先辈曾经也认为,认真吃饭、努力吃饭也会帮助宇宙克服某个节点上的困难,帮助它在既定秩序中运行。所以在新的一年里,笔者在此祝愿大家好好吃饭,不辜负每一个节庆的美食,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宇宙!但更重要的是,从节庆—神话的宇宙论思维模式中,我们也看到了古人对于天象—历法、时节、无序—剩余、死亡—幸运等现象的多维度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并没有单方面地对其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种片面且无限拔高的神圣化崇拜。这或许也是作为现代越发“单向度”的人可以从中借鉴的思维品质。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