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自然”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大重要主题,而“自然观”体现着传统中国人独特的气质品格,也蕴藏着中华文明鲜明的内在特质。无论是山水诗、咏物诗,还是田园诗、边塞诗,都承载着中国人真挚而淳朴的自然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流传于后世的诗词歌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其独有的方式抒发自我、探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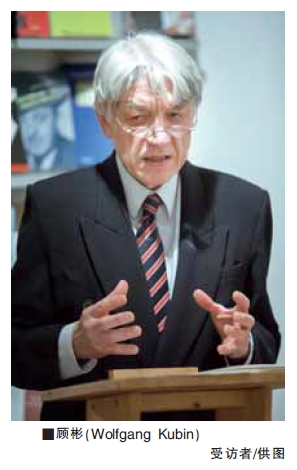
近日,中国文化史专家、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与记者畅谈他在长期研究中积累的有关中国传统文人自然观的见解。顾彬被誉为欧洲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泰斗,曾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外教中国年度人物”等诸多奖项和称号。如今,已逾古稀之年的他仍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顾彬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与自然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的发展亦是如此。自周朝以来,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传统自然观,与社会生产、历史条件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随着历朝历代的变迁而变化,映射出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轨迹。作为自然的观察者,中国文人在自然中表达认知、介入情感,将自然主观化、人格化,将景象作为思想的工具,实现了所见、所感与所思的统一。
中国作品对自然的表达远比西方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此前的研究中认为,自然是中国与西方文学作品的共同话题,但二者对于自然的呈现与表达却有很大差异。您如何理解这些差异?
顾彬:的确,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有在文学与绘画作品中对自然进行描绘的传统,然而,二者对于自然的揭示,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文化差异,且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在17世纪的荷兰绘画中,自然第一次被西方人视作独立的可以被人类所感知的风景,而直至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迅猛发展,自然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题材才真正出现于欧洲的抒情诗中,被市民阶层当作逃离闹市和反对社会制约的寄托。在这之前,西方国家艺术作品中虽然也有自然的介入,但自然只是发挥微不足道的衬托作用,既非可被单独认知的外在现实,也非人类主观意识映射的文化载体。
与此相反,在中国,早在周朝的文学作品中,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一种可被感知的观念便已初步产生,这种观念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六朝,中国文人的自然意识在文学、绘画作品以及园林艺术中得到普遍体现。而在唐代,中国传统文人自然观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为后来由宋到清中国文人对于自然的表达方式提供了范例。多年来,通过对中国文学的长期研究,我得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在早于西方一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便已存在自然观的完美表露。
与西方相比,“自然”这一术语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是仅仅指代拉丁语中“与生物(有机)和非生物(无机)现象有关的、非人为地存在或发展着的一切,即各种形式的物质”,或“一定区域内的植物、动物、水流、岩石等的总和”。自然代表着一种除自身之外的外在世界,一种能够在万物中发挥作用的宇宙间的力量,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便是早期中国文人自然观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人们把风景视作一种富有生命的真实而独立的个体,并有意识地去探求、把握它的美。
在西方文学中,对于自然的描写直至18世纪才有了一种讲究修辞的特性;而早在周朝,中国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的描写已经颇富文采、修辞华丽。在早期西方社会,对于自然的描写不一定以文学家的亲眼所见作为依据,素材来源多为“传说中的自然”,这意味着早期西方文人笔下的自然是一种脱离农业耕作、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自然。而在早期中国社会,自然观的演变脉络与农业劳作、社会生产以及特定朝代的发展变革息息相关。
可以说,自然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形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流露和表达远比西方作品深刻,自然观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人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精神支柱,代表着一种现实与情感相互渗透的寄托之物。在部分西方国家,由于文学研究方法不完备,不少学者将西方文学史的研究路径套用于中国文学,结果产生了一些理解偏差。例如,把中国唐代诗歌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相提并论。1976年,在一篇论文中,我指出了上述理解的荒谬之处。同时,在《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一书中,我也纠正了一些西方人心目中固有的关于中国文人自然观的观念偏差,即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人自然观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从三大阶段——由周朝到汉代、六朝、唐代去审视和理解它。中国诗歌是中国传统文人自然观最重要的“传播者”。此外,在赋、辞、书信体文学、游记以及写景的散文中,也可寻见中国传统文人对于自然观的表达。
早期作品反映文明与辉煌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周朝到汉代的早期中国文学作品中,传达出怎样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经历了何种演变过程?
顾彬: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诗经》中得到了典型体现。在《诗经》中,自然观的体现与当时周朝重农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兼有少量畜牧业,以木铲、石刀等耕作工具为主的早期社会,自然观反映了农民对于天气、时令、土地等的依赖。人们通过太阳、月亮、行星、泉水、雨、雪、鱼、甲虫等大大小小的自然物,船、钓具、农具、纺织品等手工艺品去认识自然、观察自然。诗歌创作灵感也因此在采集草药、砍伐木材、狩猎鸟兽等活动,以及收割、烧煮、织布等日常行为中产生。应该说,《诗经》中的自然被当作一种劳动领域的单一现象,通常用来指代人们所生存的环境中的各类自然物。在这一环境中,自然物不是抽象的,也未被美化,而是以其原始面貌出现。它们与每日的劳动生活有直接关联,对其描述构成了诗的“自然引子”。这种早期自然观更多地反映了早期中国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民间风俗。在这样一个私人财产意识尚不分明的社会,人们的自然观建立在根据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联盟和村社群落之上。
如果说《诗经》中对于自然的主观化未超出个人经验范围,那么《楚辞》则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首次以个人方式表现了显著的主体意识。《诗经》中的自然形象仍保持着一种客观的外貌,它的出现是天然的而非人为的,而《楚辞》作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其中描述的自然形象更多地杂糅着主观感受和真实所见。《诗经》中对于自然的刻画情感色彩较淡,景物看上去总还保持着景物自己,而情感色彩恰恰是《楚辞》中自然观的重要标志。在《楚辞》中,中国古代文人从自己的个体情感世界出发去观察自然,自然不再只是《诗经》中质朴形式的与农业劳动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自然,也成为尘世范围内一种有意识的私人“暗语”、自我表达的载体。兰、芷、桂、荃等自然物成为文人雅士情感表达和情绪表现的象征,对于这些景物的刻画虽来自实际生活,却又超出了实际生活的范围。与《诗经》相比,《楚辞》在情与景的表现手法方面处于更高层次,色彩更为浓重。可以说,《楚辞》中的自然主题不仅是对《诗经》的延续,更是深化。
此外,《楚辞》中的自然观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家国情怀的象征。屈原对“香草美人”的追求,可以理解为对一去不复返的“旧制度”的怀念,是一种远大的报国理想带来的“外在世界在内心的投影”。在现实中找不到施展抱负之地的士大夫们转向虚境去寻求心灵慰藉,在那个虚幻的世界,自然之物成了精神幻想之物。相比《诗经》,《楚辞》所描绘的自然现象充满着感伤,也带有些许神秘色彩和梦幻感,这一切都与当时楚地的社会背景与宗教文化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到了汉代,文学领域的写作主题与表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巩固秦朝诸多成果(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统一的文字与货币)的基础上,汉代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兴盛,经济贸易蓬勃发展,著名的古丝绸之路得以开辟。正如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所言,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去驾驭:人和自然、天和地、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以及事实上的整个宇宙。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的产生,这种自我意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为兴起于汉代的新文体——汉赋。作为一种优美而有韵律的散文诗,它们象征着一个文明高度发达、自我意识极强的辉煌时代。
一方面,汉赋中仍可以看到《诗经》和《楚辞》中的一些元素,例如宗教主题和祭歌形式;另一方面,汉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反映了汉代社会技术方面的明显进步,包括铁质工具、无轮犁、水车、独轮手推车的发明,以及100千米以上的水渠等灌溉设施的诞生。然而,与《诗经》和《楚辞》等劳动人民文学相比,《诗经》主要反映农事与耕种等百姓生活,《楚辞》则涉及对民歌进行加工并使之流传后世;汉赋既非源自民众日常生活,又非民歌加工之作,它是一种在新官僚群体中形成的“上层宫廷文学”。因此,汉赋中对于自然的描写手法也与以往传统不同,汉赋中的自然既不是与农业有关的自然,也不是带有宗教因素的自然,而是一种代表着高雅文化的自然。大规模的游猎、皇家园林仙境、鸟兽与花木、乐器与礼仪,以及一些带有异域情调的风物描写成为汉赋的典型主题。这一时期的自然观映射出一个更为广阔、完美的外在世界,同时,在《楚辞》中显露出来的诗人主观倾向在汉赋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文明是经过改造的自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六朝是自然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无论是写作主题还是作品文风,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顾彬:到了六朝,随着权力由皇室宫廷向豪门望族转移,中国传统文人的自然观出现了重要转变。这一时期对于景物的观察促使一种新的辞赋样式——咏物赋产生。咏物的对象既包括远离城市的深山老林和荒野自然,也包括乡间别墅和近郊自然。饮酒赋诗、兰亭聚会、隐居山间……文人们在探访自然、观赏风景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并寻求达到与“道”的一致、与自我的和谐。在这一时期的建安和魏晋文学中,自然观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新现实主义倾向,其中最为著名的诗作代表出自曹氏父子。曹丕的游览诗和书信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其父曹操文学作品的特点则在于对自然非同凡响的描写。《观沧海》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通篇描绘风景的杰作,成为后世典范之作,字里行间流露着诗人振奋昂扬的内心感受,映射出诗人改造现实、驾驭现实的个人决心与理想。
此外,自六朝起,“山水诗”开始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东晋最为兴旺的豪门大族之一谢氏家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严格意义上的“山水诗”创作始于著名政治家谢万,而谢灵运则将这一体裁创作推向了日臻完美的境地。在他的作品中,生机勃勃的自然之美被作为一大主题加以重点运用和描写,对自然的推崇和热爱达到了顶点,这使得其诗歌体裁十分接近“山水诗”。此外,他是第一个主张在诗歌中明确交代时令和昼夜时间的中国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在继承前朝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创新,一种新的自然观因而得以出现。同时,谢灵运作品中体现的自然观出现了从道家思想向佛教思想的明显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思想在他的笔下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与佛教思想融合为一个整体。谢灵运从佛教思想角度去观察山水,并未妨碍其以一种“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去刻画自然。在《山居赋》一诗中,谢灵运笔下的自然既是一种摆脱城市生活束缚的浑然天成的自然,也是一种初具社会文明特征的经过改造的自然。在这一自然世界中,诗人可以自由自在地驰骋想象。谢灵运用一种不含任何文字游戏的自然真实之美,一扫当时六朝文学作品的矫揉造作之风和虚幻想象。他对自然的描写专注于自然本身,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这一时期的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湛方生等人也著有不少山水诗佳作。
文明双向交流体现开放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唐代文学对于自然的描述、表达、感叹达到了鼎盛,在唐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通过自然认识自我、寻找自我、探索自我已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自然观有哪些特征?
顾彬:如果说六朝时期极大奠定了中国文学作品中自然观的基础,对后世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唐代文学则标志着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以一种成熟的方式发展达到了高峰。唐代科举制度的普遍实行,使得新型文人学士取代了传统贵族。一些文人学士诗人虽出身贫寒,却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通过他们的书写与表达,自然观在新的社会背景中产生了变化,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成为流传后世的宝贵文化财富。可以说,唐代文人将自然观彻底从贵族天地解放出来,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之上。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自然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自然观的表达深受朝廷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国家,唐王朝的繁荣程度远胜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而这种繁华也体现在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化兴盛中。中央集权机构的有效管理和内部统一,意味着“边塞”范围被纳入唐王朝统治之下,与此相关的“边塞自然”成为一些文人墨客的创作对象,他们试图将“边塞自然”与人类文明相结合,相关代表人物有柳宗元、韩愈等。此外,由国家规划并实行的大型自然改造设施,例如大运河的开凿、新式农具的使用等,深刻影响着文学家们的思想意识,对于其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华的盛世之一,唐王朝始终与欧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保持着广泛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唐文化不仅保留了自身的折中主义性质,也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性质。它在吸收中国固有文化的同时,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兼收并蓄的特性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着当时文人墨客的自然观。
二是中国文人们在其作品中“塑山造水”成为一种普遍倾向。诗人向大自然敞开胸怀,在寄情于山水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怀得以抒发。王维的“田园诗”即是一大代表。在他的诗作中,前朝两种流派的影响并存:一种是谢灵运对美妙自然的客观呈现;另一种是陶渊明“世外桃源”式的富于幻想的描写。无论是雨后新晴、空气明净,鸣叫的野鸡、茁壮的麦苗,还是村庄、溪流、河水,都展现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王维的作品中,人不再是大自然的旁观者,而是被包容进大自然之中。情与景,眼、耳、神、心全然融为一体。
三是在一些唐代作品中,自然被置于强大、高远、极富力度的视域之中。大自然代表着一种雄奇的、不可征服的存在,体现这一观念的著名篇章即为诗仙李白的《蜀道难》和诗圣杜甫的《泥功山》。此外,诗人孟郊的相关诗作也传达出类似的观念。孟郊笔下的大自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纯洁、美妙的象征;另一方面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人类面对自然肆意妄为,自然就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四是“怀古诗”在唐代大量出现。在充满着时空观念与历史特征的“怀古诗”中,眼前的自然现象使人抚今追昔,过去与现在、永恒与短暂、确定与不确定成为“怀古诗”的主题。时间的有限、空间的辽远,蕴藏在万物之中的生命力,都引起诗人的无尽思索与联想。在李白的作品《越中怀古》中,历史场景与现实画面形成对照,在这首绝句中,自然被当作一种宏阔的历史进程,体现着诗人深沉而博大的历史观。
五是唐代文人的自然观更加注重追求“风景向内心世界的转化”。自然被当作精神复归的依赖,成为文人心目中净化灵魂的力量,也成为人世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自然从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不再只属于外部世界,而变成了一种精神意念的外在表露,一种情感冲动的寄托之物,一种人物心灵的栖息之所。无论是江、山、鸟、花,还是天、雁、船、楼,都能够使诗人“触景生情”。自然的强烈象征性,使得诗人笔下的景物更多地被渲染上了人为色彩,有时不似真实的自然。与前朝相比,唐代文人的自然观摆脱了贵族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文人的观点,被文人雅士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占有。自然观成为一种景色风光与内心意识深度结合的产物,一种归于内心的情感依赖与文化象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演进史,不同时代的中国传统文人始终按照自身独特的方式去理解、呈现、书写自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人民依旧保持着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宝贵传统,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一个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作为国家治理的优先目标,这与中国文化中长期积淀而成的自然观密不可分。如今,自然观这一主题依旧吸引着众多西方学者借此去了解中国文化的故事,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质。自然观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因素之一,值得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传播、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