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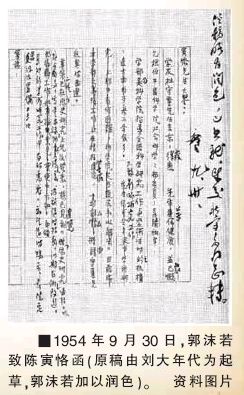
一个刊物没有好文章,地位就无法保障。《历史研究》一直与史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能够刊发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它在这一点上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在60年的办刊历程中,《历史研究》不仅见证了这些成就的取得,更是学术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创刊6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田余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甘泉先生和陈高华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历史研究》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各位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否谈谈你们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往事?
田余庆:谢谢你。年轻人是中国学术的未来,我倒是觉得你们应该更加关注年轻人,把眼光放在年轻学者身上。由于身体原因,近年来我与学术界的联系不是很多,在《历史研究》刊发最后一篇文章也是2001年的事情了。因此,我只能讲讲老掌故,可是年纪大了,能记起的老掌故也不多,过去的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我第一次在《历史研究》刊登文章,是编辑部约稿,由尹达同志召集开了个小会,周一良先生和我应邀参加。周先生是教授,而我当时只是一名讲师。邀请我撰稿,完全是提拔新生力量。我当时是年轻人,胆子大,什么都敢写,居然敢写批评胡适的文章,而且批评他的考据学,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第二篇就是《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这是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时第1期的文章。由于我之前曾讨论过曹操的问题,也写过相关文章,因此文章写得比较顺利。我记得那篇文章的语言风格与以往有所不同,在学术思想上也有所创见,即从儒法斗争来研究曹操,认为曹操在打天下时运用法家手段,但最后还是回到儒家的道路上来治理国家。这在当时还是比较新的思路。
林甘泉:我是《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老编辑,创刊60周年对我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虽然已经过去60年时间,但创刊初期的那些事情迄今仍然历历在目。关于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我曾应贵报之约,写过一篇题为《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的文章,发表在贵报“期刊”版,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一看。今天我想说的是,作为刊物早期的一名编辑,我深深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我相信,只要坚持这样一条生命线,《历史研究》的发展就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高华:我在学生时代是把《历史研究》当作经典看待的。《历史研究》曾刊发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好文章。即便是50年代发表的那些文章,我至今都能回忆起大部分,知道作者是谁。其他刊物绝对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对于从事史学研究的许多人来说,在《历史研究》上刊发文章,无异于“登龙门”。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是中国史学界的“龙门刊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界定《历史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术形象和地位?
田余庆:从“文革”以前直到七八十年代,《历史研究》无疑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只此一家。它是具有最高地位的历史学刊物,编辑部的规模也很大。那时候,谁有写得不错的文章,就想着投给《历史研究》。后来,学术发展有了一定的深度,《历史研究》的发稿范围由最初的中国史拓展到世界史,再将近现代史囊括进来,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一些青年学者引入西方的学术方法,以推进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有观点认为,这造成了老一辈学者和年轻学者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代沟。依我看,现在上一辈都没剩下什么人了,代沟也应该不存在了。我自己脱离学术环境很久,既不老,也不年轻,属于“超老”。
陈高华:《历史研究》从一开始的地位就不同于其他刊物,在史学界处于领导地位。虽然后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它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在中国史学期刊界就是“老大”。《历史研究》刊发的文章,总体来说质量是比较高的,往往会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它的权威性所在。一个刊物没有好文章,地位就无法保障。《历史研究》一直与史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能够刊发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它在这一点上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
2引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史学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都有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政治史研究似乎有些停滞不前。您如何看待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历史研究》在这方面应如何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田余庆:社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统治系统,没有统治系统也写不了历史,这个系统除了政治还能有什么系统呢?脱离开政治史,单纯以经济史为系统写一部通史,恐怕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的组织就是这样。无论中外,也无论哪一个朝代,都是如此,这样才会有历史,才有历史学。至于政治史搞偏了、观点不对头,那是做学问本身的问题,不是政治史要不要的问题。过去搞政治史,未见得搞通了,政治也是有表象、有内涵的。在表象上,你也描他也描,描得千篇一律,就没什么意思了。但是,要真正把政治面目勾画出来,并非人人都想得到,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深度研究。我们是否对中国每个朝代都进行了这样的研究?并没有。
政治史本身没有错。任何一个国家写通史,都要以政治史为主干。问题就是有些东西只适合做专史,不能拥有政治史那样的地位。在政治史研究中,资料搜集占很大比重,前期工作要付出很多,搞政治史就像爬喜马拉雅山,爬一千米、两千米的人很多,但真正能接近顶峰的人就很少。在这个位置上,要上升几十米都是非常困难的,而难爬的这块地方,愿意去爬的人也很少。《历史研究》应该引导更多的人在学术高峰上勇于登攀,一往无前。
陈高华:我们对其他问题做一些广泛的研究,再回过头看政治史、经济史,可能会有一些新发现。过去,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上。改革开放后,很多新的问题被提出来,新的领域也得以开拓。我想,这些新问题、新领域的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就可以再攀登一个新高峰。其他领域的研究是基础工作,基础不雄厚,总是纠缠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做文章,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最明显的就是思想史。到了后来,我觉得思想史研究很难搞下去了,想写出好的思想史文章很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那就是先在其他领域进行突破,把文化史、社会史做大,再回过头来看思想史,很可能会提出新的问题,促使思想史研究再进一步。我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历史研究》在社会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史等方面,发表了不少笔谈或专题文章,在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林甘泉:这可能涉及现在普遍提到的碎片化问题。我虽然不反对碎片化,但具体问题的研究要区别开来。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要充分尊重其个人自由,他喜欢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但对一份刊物来说,就应该避免同质化倾向,要强调“百花齐放”,不仅是理论和见解上的,也包括题材上的。《历史研究》作为一家具有60年历史的刊物,要时时考虑自己的定位问题,要形成自己的办刊特色。《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一般性的史学类专业期刊,不需要求全,也不能跟风。具体来说,不能来什么文章,觉得不错就发,要引导学术就不能这样做。当今学术界的理论基础较为雄厚,文章也都是比较扎实的,是不是这样水平就高呢?未必。面对史学研究的不良倾向,编辑部近些年敢于表明态度,通过举办历史学前沿论坛、加强选题策划等手段,告诉我们需要怎样的史学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效果。
陈高华:实际上,碎片化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研究具体问题、“小问题”,这本身并不能说是错的。史学研究,既要研究大问题,也要研究小问题,这是互相促进的。但是,如果总是研究小问题,而不能以小见大,这就会导致碎片化,并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两类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讨论理论就可以避免碎片化,这种想法太单纯了,我不赞成。史学研究如果不去做一些具体研究、不关注一些小问题,那么,大问题的研究就缺乏支撑,也会出现片面化,甚至一般化。反过来说,只注重小问题,忽视大问题,眼界就会太小,难有突破。年轻学者如果能够理清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意识地从小问题做起,将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逐步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一条好的发展道路。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朵金花”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研究的结果。各位先生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的影响?
林甘泉:现在有人鄙薄“五朵金花”,但是他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正是得益于“五朵金花”的研究,今天的人们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性质有了深入、丰富、立体的认识。如果要写一部新中国以来的史学史,离开“五朵金花”这个骨架,还能写什么?应该承认,围绕“五朵金花”的文章质量有高有低,也有观点片面者。但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清经济史之所以成为很重要的领域,吸引诸多学者投入精力去研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提出有直接关系。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推动下,明清经济史才有现在的丰硕成果。《历史研究》在引导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方面,是有独特贡献的。
陈高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对史学研究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现在不少人强调并放大与此相关的消极方面,这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我们强调学理论,强调研究大问题,“五朵金花”是典型的大问题,为史学界提出了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历史研究》曾围绕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等问题,发表过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它们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并重,做到了史论结合。“五朵金花”的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就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思中国历史的时候提出来的。学了唯物史观,再来看中国历史,就知道土地制度是根本性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很自然地提出这些大的问题来,推动大家讨论,这是学习唯物史观的好处。
我觉得“五朵金花”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五朵金花”。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历史分期,确实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事件,对中国史学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能够成体系地讲出来,对史实的考订也比以前进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翻检当时的目录,不难看出,《历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学界深化中国史研究方面,旗帜鲜明、厥功甚伟。现在一些媒体过度吹捧新中国成立前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就,仿佛我们的史学研究水平还不如过去。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发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史料,也提出了很多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整体上将我们的研究水平、认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林甘泉:现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很少甚至根本不提“唯心”、“唯物”,好像这个问题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存在不存在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有“唯心”、“唯物”之分的。国外学者有时候比我们更注重理论研究,倒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有多深入,但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别致的。
田余庆:这一点我同意,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往往没有外国人研究中国那么深入、透彻。以中国史研究为例,外国人研究的深度,与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外国人好像更能进入到中国内部来,而我们要想深入外国社会之中,则没有那么容易。这是整体学术水平的问题呢,还是历史的原因呢?《历史研究》也应在这方面引导人们去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努力深化中国学者对国外史学研究的认识。
陈高华:中国缺乏研究他国的传统,没有基础。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东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从来都是他国研究中国,而中国没有研究他国。像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尤其近代一百多年,就是为了侵略,这是花了功夫的。例如敦煌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现在则不同,在中国古代史很多领域,我国的研究是领先的。再如在藏学研究领域,以往中国学者根本沾不上边,但现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林甘泉:我还想从思想层面谈一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不要坚持。从学者所做的研究中,是能看出其指导思想的。何兹全先生曾对我谈到,现在各种新潮的意见,他觉得多数都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具体认识可能需要不断完善,但有一条,其经济形态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否定的。对此我有同感。谁都没想到今天的世界能发展到这个水平,人造器官都出现了,社会结构和关系还要完全按照一百年前的理论去套吗?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必定会改变人类的一些观念,社会也在变化。但是,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是得讲,只不过新的形势下要用新的材料和词汇来解释。怎么解释、怎么讲,都可以敞开来讨论。
4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历史研究》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取得更大的成绩,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田余庆:办好《历史研究》,需要大力开发编辑部同志们的智慧。从一个作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些以前不为人所注意的课题,仍有待于从政治史角度进行深入发掘。举一个例子。前些天,我关注了一下土司制度和文化,以及改土归流方面的前沿问题和专门的学术会议。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史问题,可是现在学界没有把它当作政治史来看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有人大书,却没有大议,没有人将其提升到国家政治制度层面来研究。因此,政治史的很多领域,我们没有去关注。《历史研究》是否能从引导学术发展的角度,组织相关文章进行讨论,进而推动政治史的发展?这类问题都值得考虑。
林甘泉:《历史研究》走过了60年,与我们创刊时完全不同了,当时创刊就是对学术的一大推动,写一篇文章发表一个见解就是有学术性的。现在呢?中国史、世界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具备了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如何在这些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学术性。作为一份全国性的一流刊物,《历史研究》在学术上要有雄厚的根底,能经得起推敲,每一期都要有几篇学术性强的文章。二是理论性。《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要注重理论性。现在,中国史研究最薄弱之处就是理论性缺失,将来可能会出现危机。如果能在学术性和理论性两方面守住阵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陈高华:中国现在的刊物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么多刊物没有必要。刊物过多,意味着水平下降。很多刊物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只有少量刊物能够保证质量。《历史研究》的稿件质量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它的选择余地大。竞争是有,但不用害怕,虽然刊物多,但实际上获得学术界认可的,也就是那么几种。只要我们能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主动地应对挑战,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现在史学界最大的问题是讨论不起来,很难像以前那样针对某个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不管是史学,还是哲学、文学,如果没有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对学科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历史研究》还是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需要刊发一些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当然,组织这样的文章确实有难度。就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情况来看,年轻学者还是偏向于从事具体研究,对理论性的问题关注较少。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也离不开理论,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将学术做大做好。实证主义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不能过分夸大,但它是基础。要做到理论与实证有机结合,实证做得好,理论就能讲得透。我们希望《历史研究》在这方面成为中国史学界的表率,期待着《历史研究》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