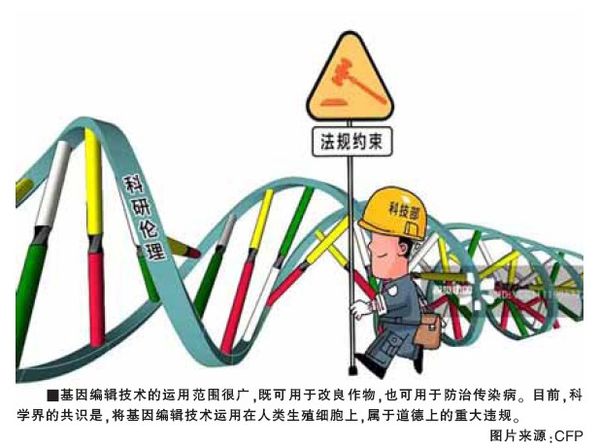
代际正义、排外主义、恐怖主义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对当今世界人类的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道德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行动的规范,对于解决这些难题有着关键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理论家和科学家试图通过“生物医学道德增强”(Biomedical Moral Enhancement)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基本理念是,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如刺激神经、药理和基因干预,增强人类的道德能力,从而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其中涉及的道德能力不仅包括共情、信任等人类道德情感,而且包括一些与道德相关的认知能力,如理解道德判断和行为后果的能力。
理解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新进路
实际上,人们可能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并不陌生。2018年轰动一时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借助生物医学的手段干预人类的基本能力,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道德问题。在过往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研究者都是通过应用某种已有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某个维度进行伦理评估。比如,支持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能否在后果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坚信道义论的理论家则担心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对人类尊严和自主性构成威胁;还有一些理论家着眼于人权理论,担心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会侵犯人权或存在强制施行的问题。尽管这些理论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规范人类道德增强问题的不同思路,但这些做法往往都预设某种规范伦理学理论的正确性或依赖对某些内在价值的证成。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将这些理论应用在人类道德增强问题上是合理的。不幸的是,在何种规范伦理学理论是道德真理以及尊严和自主性究竟是不是一种内在价值问题上,哲学家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道德演化论思想为人们理解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提供了一条新进路。道德演化论的研究进路致力于将人们普遍认同的演化科学理论应用于道德领域,从而为道德的功能、人类的道德心理及其演化过程提供一套自然主义的解释。从道德演化论的角度来理解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具有如下优势:第一,跨学科的性质使得这一进路能够充分利用各个学科的资源和方法。不同于以往纯粹的规范伦理学研究进路,道德演化论将伦理学、政治哲学、人类学、生物学、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概念和方法论资源整合了起来,因而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第二,以往的研究进路往往只能从一个维度来探讨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但道德演化论则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提供了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解释,并将其建立在一种道德起源的自然主义解释之上。这也使得它并不依赖某一特定规范伦理学理论的真理性。
在道德演化论的视域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人类的道德心理与道德能力受到了演化而成的自然限制。根据道德起源的演化论解释,人类的道德是演化而成的。具体而言,道德最初是人类为了适应史前恶劣的生存环境演化出的一种适应性产物。它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社会行为和管理社会成员的内部冲突,从而增加人类的繁殖适应性。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通过考察道德产生初期的自然环境以及演化过程对人类道德心理的影响,认为“人类道德心理的核心元素是在中到大型民族语言群体之间的冲突中形成的。并且,由对群体内的偏爱和共情以及对群体外的敌对和反感结合而成的‘狭隘的利他主义’,是人类的道德心理中最具跨文化性的强大特征之一”。根据这种解释,那些能够演化出并遵循道德系统而行动的群体获得了更大的繁殖回报,而没有发展出这种道德的群体则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演化保守主义与演化自由主义之争
这种对道德起源的演化论解释很好地说明了人类道德心理在共情力以及包容他者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然而,在人们该如何根据这一事实进行道德建设的问题上,道德起源的演化论解释内部却分成了“演化保守主义”和“演化自由主义”两个阵营。“演化保守主义者”认为,演化而成的道德心理只能支撑起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正如斯蒂芬·阿斯玛(Stephen Asma)所指出的,人类的道德情绪“不能无限延伸到陌生人和非人类动物的广阔领域中”,进而人类的利他倾向也只能作用于与他们具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情感共同体”。所以,人们应当减少相应的道德规范或降低道德要求,以使道德规范与人类的道德心理相匹配。与此相对,“演化自由主义者”则主张,人们应当为了使有限的人类的道德心理符合于现代道德判断而努力。只有突破“狭隘的利他主义”才能应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紧迫道德问题。
随着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道德增强使一些“演化保守主义者”看到了突破演化限制的可能性。因此,他们与“演化自由主义者”在实施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上达成了共识。既然仅仅依靠自然演化的人类心理,无法帮助人类摆脱史前道德遗留下的排外性和狭隘性特征。那么,为了解决现代生活中那些最急迫的重大道德问题,我们必须借助生物医学的技术手段,通过改变人类的生物学基础进行道德增强。像英格玛·佩尔松(Ingmar Persson)和朱利安·萨乌勒斯库(Julian Savulescu)所说的那样,人们演化形成的“道德心理是‘短视的’,它们仅限于关注附近的人和不远的未来”,而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这种演化而成的道德心理显然已经不再具有适应性。因而我们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把他们道德关切的范围扩大到熟人构成的小圈子以外,甚至将未来的子孙后代也包含进现代人的道德关切之内”。
事实上,“演化保守主义”和“演化自由主义”就像是一体两面。他们都对人类道德心理的发展持有一种悲观态度——人类道德的发展完全受限于史前的演化过程。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演化自由主义主张大胆地运用生物医学技术,帮助人类缩短道德心理和道德能力演化进程,通过人为的干预和设计,使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在短时间内的巨变。实际上,这种主张得以成立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借助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的道德能力确实能够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从而解决现代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而如果采取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手段,不一定能够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并且我们还能找到其他提升人类道德能力或者解决现代社会突出问题的替代性方案,那么鉴于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风险性,我们就应该更加谨慎地考虑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使用。在这里,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生物增强技术进行一种生物文化学的分析。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风险与局限
佩尔松和萨乌勒斯库提出的道德增强的主要方案是,通过为人体注入类似催产素等会影响人类道德情感的激素,增加他们的共情能力,从而让人们产生更多的亲社会反应。但我们至少有三个理由来质疑,这种方案未必能更好地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第一,虽然共情能力可以通过人们的情感反应,促进他们对他人的关怀,但正如杰西·普林斯(Jesse Prinz)提醒我们的:“共情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换言之,人类共情能力的发挥往往受限于时间和空间。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对与他们产生过直接接触的群体产生共情。较之遥远的陌生人,人们的共情能力总是先作用于自己群体内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共情能力的提高不一定会促进人们更好地遵守普遍的道德规范,而且在群体间存在资源竞争的环境中,更强的共情能力反而会加剧人们对外部群体的排斥。第二,激素水平的波动与共情的产生可能只具有随附关系而不具有因果上的关系。共情的发生往往与个体的认知乃至过往的经验相关。如果一个人缺少关于某种经历的体验,那么他可能无法理解那种经历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一种苦难,因而几乎不可能对那种经历产生共情。根据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人类共情机制的解读,共情本质上是一种将行为主体自身的情感和遭遇投射到对方身上的过程。这个过程难免会受到主体自身经历的局限性和常见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并不一定能促进共情能力的拓展。第三,共情意味着一种对特定对象的额外关注和重视,因此共情能力本身也可以导致一些不公正的行为。比如,鲍威尔(Russell Powell)指出,共情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他们感同身受的人,但这种关注是具有偶然性的,另一些没能与之共情的人可能被不公正地忽视了。可见,佩尔松和萨乌勒斯库的道德增强方案并不一定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正如鲍威尔指出的,“当道德陷入群体认同、局部性和具体性的危机时……增强一些亲社会性的生物学基础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道德问题似乎并非源于缺乏共情力本身,实际上我们现有的共情力是足够的,但它很容易受到操纵和误导,从而助长了群体间的冲突或使得人们的关怀圈子只能局限于群体内部”。
实际上,以上问题不只是企图增强共情能力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方案所需面对的,任何期望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单纯地增强某种“道德能力”的尝试,都可能无法实现它们所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道德不只是一种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立场称为生物文化演化论。根据这种立场,与我们狩猎采集的祖先相比,现代人类的道德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性和利他性。这种道德进步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道德教育与社会文化建设。根据生物文化演化论的分析,那些现代道德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某些道德能力的强度不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缺少激发或促进人们道德能力的条件。生物文化演化论提醒人们,生物学基础不是人类道德心理和能力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文化建设与道德教育对塑造人类的道德心理以及培养人们的道德能力发挥着巨大作用。而文化建设与道德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社会的物质繁荣与社会总体认知水平的提升。历史上,许多重大道德进步,都建立在一系列社会文化条件得以满足的基础上。比如,印刷机的发明;社会识字率的大幅提高;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等。
因此,如果想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道德挑战,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也许并不是最好的出路。首先,由于生物医学技术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改造具有不可逆性,这种手段比借助社会文化手段具有更大的风险。其次,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实施过程会改变或剥夺人们的情感、经验甚至记忆,可能带来人格同一性的问题。最后,由于特定的道德能力可能在某种环境下被扭曲,甚至被利用。因此,仅仅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增强道德能力,而不进行道德进步所必需的社会文化革新,不但无法解决现代道德问题,而且会使解决问题的手段变成问题本身。就目前而言,增强道德能力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创造出更有利于道德教育的包容环境来促使人们道德能力的提高,同时通过改善那些会助长排外与歧视的社会因素来抑制人们的排外主义道德反应。
综上,对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道德挑战而言,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可能既不必要,也无法起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生物医学技术的风险完全可控,以及研究清楚道德能力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发展机制之前,我们都应该谨慎地看待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计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