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对孙犁的叙述往往聚焦在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上。孙犁擅于运用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以开放自由的行文结构,包蕴诗性的语言质素,为小说赋予“诗性”的特征。身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孙犁,始终还有着一个不灭的诗人梦。1982年12月,在给贾平凹的信中,他曾自谦地说:深知自己诗歌写作中的毛病,但要是不再写诗,又于心不甘,所以便“硬往诗坛上挤”,即使当不成诗人,弄到一个在“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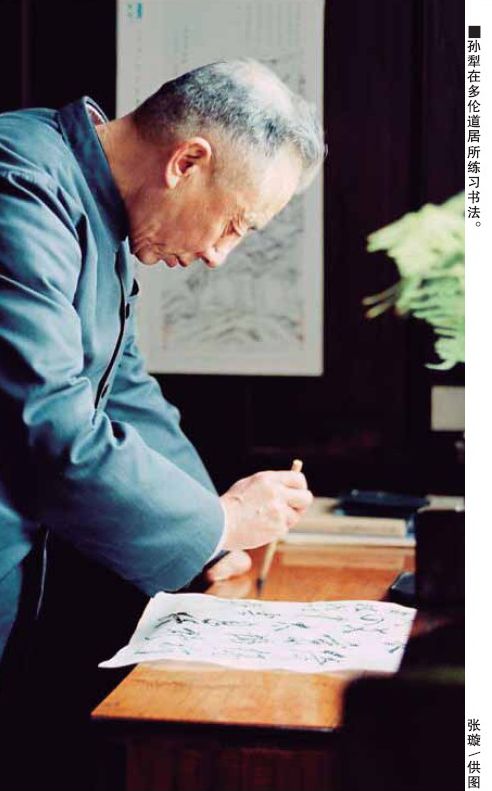
实际上,孙犁写有相当数量的诗歌作品,有多部诗集出版。如《山海关红绫歌》(知识书店1951年版)、《白洋淀之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孙犁诗选》(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孙犁新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多个阶段,孙犁均有相应的诗作问世。这些文本意象清新、叙事流畅、形象生动、语句短促、语言质朴,展现了作家对诗歌艺术的独到体认和对自我生命的深邃理解。
回顾孙犁的诗歌创作,当从1934年4月说起。他以笔名“芸夫”发表诗歌《我决定了》,刊于4月26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这应该是目前能看到的孙犁最早的诗歌作品。诗中的抒情者以决绝的姿态告别家乡,投入城市的怀抱。然而,生活上的失意、心理上与城市的隔膜,使得抒情者眼中的城市遍布着丑恶。秉持社会性的观察视角,孙犁揭开了都会繁华表象下“一部分的人,/正在输血,/给那一部分的人”的剥削本质。可以说,《我决定了》奠定了孙犁诗歌中抒情主体的精神特质,他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言志”的传统,又能真诚地投入时代现实,打磨个性鲜明的主体形象,从而开启了一个缪斯追随者的寻梦之旅。
孙犁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1943年,他在冀中工作期间,先后编辑完成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海燕之歌》,写作《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春耕曲》《大小麦粒》等叙事长诗,这是孙犁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集中阶段。对于这一时期写诗的经历,他曾自述道:“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这些叙事长诗注重文学的宣传和鼓动效应,内蕴革命文化的道德伦理。作家塑造了儿童团长小金子、梨花湾的抗日战士李俊、妇救会会员王兰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尤其是《白洋淀之曲》中的水生、菱姑等形象,为其日后的“白洋淀”叙事奠定了基础。
1949年初,《天津日报》创刊,孙犁任副刊科副科长,除夕作《山海关红绫歌》,次年5月作《小站国旗歌》。他热衷于民间说唱的艺术形式,文本融入了大鼓词、梆子戏等艺术元素,以此配合文艺“大众化”的趋向。进入新时期,孙犁再次迎来诗歌写作的高峰,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新的政治、文化精神感召下,孙犁的写作接续当代文学中浪漫抒情与时代现实相结合的传统,同时也流露出浓浓新意。他找到了一种与内心需求相一致的表达方式,多采用直抒胸怀与触景生情式的艺术手法,以简省的笔调、直白的语言和通透的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代变化和思想运动,诗歌创作进入了“情”与“质”共生的飞跃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真理的执着探问和深入掘进。孙犁的诗中处处彰显着抒情主体的理想主义精神,如《柳絮篇》所写:“给我时间吧/我要再去探索它/追求它//美和真诚/是永久存在的/是到处都有的/是不可战胜的。”文本延续的依然是作家在处女作《我决定了》中表达的崇尚真理的精神。他还写有一些纪怀类作品,如《寄抗日时期一战友》《悼念小川》《吊彭加木》等。在《吊彭加木》里,作家一面用自己真诚的感情缅怀彭加木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一面对那些诽谤、中伤彭加木的人予以抨击:“你死后/还有流言蜚语的风沙/想掩盖你的英灵/造谣者失败了/他们的身价/不及一粒真正的沙土。”对彭加木的赞颂,实际上就是对追求真理的肯定与向往,一切阻挡真理的人性之恶,亦成为作家在诗歌中反复鞭挞的对象。
二是彰显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孙犁希望用文字表达个体与时间竞速的急迫感,他强调以反思精神进入历史,情感内敛、不徐不疾。如“童年纪事”系列篇章中,孙犁调用舒缓自如的散文笔法,诉说幼时的生活记忆,不时显露出童趣稚拙的一面。细究内里,仍能读出文字背后的反思意味。《燕雀篇》中植入了孙犁对“除四害”运动中麻雀遭遇的慨叹,《猴戏——童年纪事》里写到他在观看猴戏时,被一只猴子“惊恐的眼神”深深触动引发的精神痛感。孙犁避免机械复述、展示历史事件,他选取常人习焉不察的生活片段,把叙事、抒情、绘景融为一体,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使反思精神得到具体化呈现。
三是哲理意识的贯入。孙犁的诗歌扬弃了纯粹浪漫式的主观抒情,走向更为沉静的精神内省,使情感在隐显之间张弛有度。这种哲理式的书写方式,很能代表20世纪80年代一批回归文坛作家的艺术风格。通过对生活之美的创造性悟读,孙犁持续着对“美”的挖掘。透过生活的细节,他以富有思辨力的阐释将诗歌引入哲学之境,有效处理了浪漫抒情与朴素说理的关系。他深知,诗歌的目的并非要使人远离烟火气,滞留在超现实的虚境,而是要给予读者深刻、厚实的思想启迪。说到底,便是平衡艺术信仰与生活现实的关系,将诗歌导向因终极关怀而产生的、趋向人类本质的哲理内涵。所谓哲理,在孙犁那里又是从生活的变化中推演出来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于是,在写作中,孙犁不断调整着思维的精度,强化着“思”的品格。看《海鸥》一诗,诗篇由四个场景组成。作家先写第一次见到海鸥的观感,认为它是一种纯洁的神鸟,然后提到自己的海鸥牌手表损坏,继而引发他从对手表的思索转为对鸥鸟的喟叹,不断追问它是如何面对大海和风暴的。显然,失灵的手表,风暴中的鸥鸟,对应的是作家生命中某些黑暗的困境。他要做的,便是像礁石一般,不被“海水冲垮”。如艾青的名篇《礁石》一样,孙犁笔下的“礁石”也是其精神品格的外化物,蕴藏着作家的生命强力。
在孙犁晚年的文学创作中,他经常俯瞰一生的命运轨迹,尝试进行总结性的书写,如《希望——七十自寿》等诗,很能代表作家晚年的人文精神。这些作品熔铸了希望与失望、痛苦和欢欣,常以“少女的话语”“小鸟的鸣叫”等事态化意象展现。他曾自谓“老树”,虽“经受的风雨太多”,但仍然“童心不死”,希望逢着生命中遇到的“小鸟”和“小花”。但鸟儿终将飞走,花朵也要枯萎,于是抒情者感叹道:“老树开始了叹息/它如此命薄/它不再幻想/不再盼望/它也不再自作多情/它要聚精会神/一如既往/有始有终/完成自己平凡的生命。”(《老树》)可见,孙犁坚持书写自我,却从不神话自我,不扩张自我意识。他主张“诗贵有我”,强调展示自我的真实面影,即便是弱点和痛楚,他也不刻意避讳,其生命境界趋向于达观自足。
始终忠于现实并与之保持有效的对话,这成为孙犁创作的重要精神向度,其间蕴含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作家心中坚定不渝、对自我主体性精神形象的持续探问。尽管孙犁说自己写的都是“一些近于散文的诗”,但这些作品更为直接地彰显了其文学创作中的“诗性”美。孙犁的诗歌熔铸了他的文化心态史和精神求索史,切实参与并支撑了20世纪新诗的思想与美学建构,理应为我们所重视。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