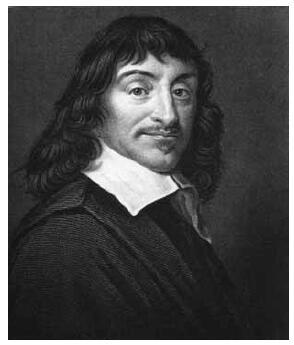
笛卡尔 资料图片
机器与有机体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相似性,它们都是由一些功能各异的部分构成的整体,都有自身的生命周期,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功能失常和组织解体。因此,一部分哲学家(如笛卡尔和维纳)主张通过机器来理解有机体,形成了有机体的机器概念;另一些哲学家(如康吉莱姆和西蒙栋)则倾向于通过有机体来理解机器,发展出了机器的有机体概念。然而,当他们以不同方式将机器等同于有机体时,却违背了我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常识:机器与有机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因为机器的行动目的是人类设定的,而有机体的行动目的是内禀的,所以有机体具有真正的能动性,而机器只能听从人类的意志和命令。如此一来,从上述两种概念出发来思考机器(和有机体)的能动性,将会得出一些超出常识的结论。它们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机器力量仿佛具有了自主性的时代里,人类究竟应该如何与机器共存。
有机体的机器概念
笛卡尔是有机体的机器概念的始作俑者。他把心灵规定为不占据任何物理空间的实体,并让其从物质世界中撤出,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成了由各种器官构成的机器,遵循着因果定律而运转。心灵和机器因此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设想,即便一台机器外形仿佛人类身体,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动作,我们也可以分辨二者。首先,人类可以灵活地使用语言,但机器只能按照设定的规则说出某些词语;其次,人类具有通用的智能,机器即便在某些专门功能上做得比人更好,却无法像人类一样可以做其他事情。人之所以具有这些独特的能力,正在于他的理性灵魂;而机器由于欠缺理性灵魂,无法做出基于思考和推理的行动,“它们的活动所依靠的并不是认识,而只是它们的部件结构”。笛卡尔的这一设想,标志着有机体自然观的彻底败北,但也意味着人本主义的发扬光大。他一方面把有机体(包括动物和身体)贬斥为机器,另一方面又赋予人类无上的优越性。人的尊严就在于他的心灵,心灵具有能动性;世界成为一部机器,机器遵循因果性。
机器的时代就是控制论的时代,笛卡尔之后有机体的机器概念被继续推进,人类优越性的本体论主张却被抛弃了。1943年,诺伯特·维纳与其他控制论者合作发表了著名论文《行为、目的与目的论》。他们强化了有机体的机器概念:“动物与机器中广泛的行为都是相似的。”他们也颠覆了人类优越性的主张:人具有的目的论行为就是负反馈机制,动物和机器同样具有。于是,灵魂的理性能力不再为人类独有,足够复杂的控制论机器一样可以掌握。在人工智能兴起的前夜,维纳畅想:“随着关于胶体和蛋白质知识的增长,未来的工程师可能会尝试设计这样一种机器人,它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结构上都类似于哺乳动物。”维纳信心满满,在他看来智能机器或赛博格的能动性,与有机体的能动性并无不同。这预示了不久之后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对人本主义者的嘲讽:与智能机器相比,人类并无任何先天优越性。随着人工智能在棋牌游戏上战胜人类,我们似乎不再怀疑,机器将会插上能动性的翅膀,把人类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无论维纳如何把有机体视同机器,如何抹去人类的先天优越性,他仍是一个老派的人本主义者。在控制论开始大规模应用于社会控制和军事的时代里,他忧心忡忡地谈论着机器对人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碾压。这种担忧正是人本主义者的技术恐惧症的一个变体。正如兰登·温纳所指出的,机器的巨大力量引发了人们对技术失控的担忧,机器开始被“描绘成几乎有生命的某种事物”,它“具备了生命特性——意识、意志和自发运动,这些特性使它与人类社会相对抗”。这种技术有灵论往往伴随着一种顽固的人本主义,机器力量被视为人类力量的异化。我们所创造的机器的力量越是强大,我们自身就越是贫瘠和干瘪。人本主义的理想是让人成为机器和自然的主人,但在现实面前,机器却获得了一种主人式的权力,人反倒失去了一切自主性。机器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工具,人类被这一异己的力量置摆、促逼。
机器的有机体概念
正是基于对机器力量的深刻感受,机器的有机体概念悄然兴起,而有机体的机器概念则受到广泛质疑。笛卡尔和维纳试图从生物学中排除目的论,但法国科学哲学家康吉莱姆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不过是一种错误的幻觉。康吉莱姆详细解读了笛卡尔的文本,发现他根本无法完全排除目的论,因为机械论仅能解释已经存在的机器如何运作,却无法解释机器是如何被建造的。实际上,只有理解了机器的功能和目的,才能进入机器的形式与结构。如果承认了机器的目的论,就有必要用有机体的模式来理解机器。康吉莱姆引述了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兰的观点:技术作为有机化的物质,有着自身的演化历史。机器就像有机体一样,有对环境选择的适应,有自身的目的论。我们不应该如控制论那样把生物视为一种机械现象,而应该把机器视为一种生物现象。如此一来,机器也和动物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能动性。
然而,机器的能动性并非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力量。勒鲁瓦-古兰用技术与人类的互补性来解释技术的演化动力。技术演化是一个从内在环境出发,逐渐攫取外在环境的过程。内在环境就是技术所关联的族群所共享的文化,外在环境就是一个族群的物质环境和异族文化。正是内在环境赋予了技术以意向性,并在与外部环境的碰撞中不断地将其转化为内部环境。与作为人类学家的勒鲁瓦-古兰不同,作为技术哲学家的西蒙栋在《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中试图论证,技术客体凭借着一种独立的逻辑而不断演化,人类文化并非技术客体的意向性根源;相反,人类仅仅是技术意向性的执行者。在西蒙栋那里,机器具有了更强大、更独立的能动性。
西蒙栋用个体化(individuation)或具体化(concretization)来概念化技术客体的演化过程,它呈现为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个体发生过程。最原始的技术个体是抽象的,本质上是科学概念和原理的物质转译。它的每个部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和明确的功能,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机械地聚集在一起。充分演化后的机器是具体的,它更接近于生物个体的自然系统。此时,技术个体包含的技术元素之间的内部共振(internal resonance)增强了,一个技术元素往往具有多重功能,同一个功能也可以分别由几个协同关联的技术元素来实现。西蒙栋特别以发动机的历史来佐证这个观点。他认为,老式的发动机是抽象的,而当代的发动机是具体的。因为老式发动机的每个要素都有独立的功能,它们在热力学循环的某个时刻介入之后,就不再对其他元素产生作用。相反,现代发动机的各种元素之间相互影响,活塞、汽缸盖、火花塞的各种特性与发动机的热力循环之间,彼此像有机体的器官一样相互关联在一起。因此,技术的演化就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具体化过程,同时也是机器不断个体化的过程。
西蒙栋特别思考了具体化过程中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在他看来,技术个体就像生物系统那样具有自己的关联环境(associated milieu)。在具体化的过程中,技术个体日益把其他自然事物和技术客体作为自我维持的条件,而不再完全依赖于人工介入和人工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技术客体留下的复杂的世系,展现了一个充满了成功与失败的演化过程。演化成功的技术客体总是比它的祖先实现了更好的功能和结构整合,它的技术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而变得更加具体化和更少抽象化。因此,具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技术个体适应、吸收和改变环境的过程。
如何与机器共存
在勾勒从有机体的机器概念到机器的有机体概念的思想史转变轨迹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机器能动性对人类自由的威胁。有机体的机器概念总是非常矛盾地与人本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笛卡尔和维纳在把有机体还原为机器的同时,却又把人类价值置于一个崇高的位置。他们都持有这样一种人本主义信念:将机器与人类对峙起来,让人成为机器的主人,而不是被机器奴役。维纳不无担忧地指出,机械化的发展将会让整个世界成为一部超人般的机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为了给个人权利和自由留下空间,就必须限制机器在社会中的应用。
与之相反,机器的有机体概念则预示了一种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价值观:机器总是与人类协同演化,人类的解放同时也是机器的解放。西蒙栋没有全然反对人本主义,但他激烈批判了一种肤浅的人本主义。后者一方面将技术客体视为无意义的物质装置(如笛卡尔),另一方面又将机器视为具有敌对意图的事物(如维纳)。这是因为它把文化与技术对立起来了,然而技术恰恰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更新人本主义,就必须把技术性带入文化之中,从而重新思考人类的异化境况。在西蒙栋看来,异化的根源是机器的使用和建造的分离,劳动者成为机器的消极的操作者,而不再积极参与机器的建造、发明和重构。这意味着,通过参与机器的设计,把人类和生态需求整合到机器的具体化过程之中,将会克服机器与人类的异化。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限制机器的应用,而是重新设计并加速机器的应用。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延展心灵中的物质能动性问题研究”(GD16XZX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分析哲学国际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