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常认为,庄子(作为个体思想家与学派的统称)是美学意义上的“自修”者,致力于自我之精神修炼,以达至“逍遥”之境。然而,我们不应误解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形象,认为庄子专于修“己”而对他者有所忽略。事实上,庄子特别关注建立与他者的“友谊共同体”。通过“相忘”与“道术”,他将“己”与“人”之合作建立在真正道德的心智基础上,以此成立颇具吊诡意味的“友谊共同体”。
“友”的拣选机制:莫逆于心
“朋友”属于人伦关系,在不同思想学派那里,对“朋友”关系不仅有着评价态度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理解视角不同的问题。在先秦诸子中,庄子于人伦关系中特重“朋友”一维,这点颇可与早期儒家的视角作比。孔门其实亦重“朋友”,《论语》首章《学而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即显明此点。儒家谈“友”,是从己人对举角度入手,突出相互的“知己”性。相较于儒家“友”之“知己”性,庄子一派对“朋友”的理解更重“伙伴”性,即能够共同参与某一“空间”“场域”游戏之“同行”,故而就格外凸显了“朋友”的“相与”性,即“个我”之间成为“游戏”伙伴。
当然,要加入此游戏伙伴圈进而相与为友并非容易之事,需要相当之“心智”条件作为前提,其根本在于对“生死”大限的突破。在《庄子·大宗师》中颇多此例,比如“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为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在此,有一个“拣选”朋友之机制,即能够通过“言行”显示其通达生死一体、随顺大化者,才能被“确认”为“友”,因而“相与为友”其实是“个我”之间交互“拣选”的过程,其评价之标准即是他们之间“不约而同”的“默契”。有此“默契”,即成“友”;无此默契,即失之交臂。事实上,庄子之所以以“生死”大限的应对来考察友之与否,在于“安时顺化”所指向的对“自我”身份的丧解(无己),由于拆解了“是己”之心,故而“顺化”,并消解了“辱人”之心。
也许我们会认为,庄子所说的这种“莫逆于心”的“默契”有点“玄乎”,但其实如是“择友”非常“实在”且“有效”。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空间里,“个我”之间并非完全“熟知”,而是处于“相互不知”的状态,因而“他者”之“心”,包括其兴趣、爱好、信仰、立场等,并不全然为“我”所了解。在此情形下,寻求一个能与“己”同“游”之“友”者,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发出“求友”之信息,所谓“嘤嘤其音,求其友声”。“求友”之信息自然不是通过“媒体”的途径,以“正儿八经”之形式“广而告之”的,而是在非“正式”场合,以一种“私人”交谈的形式发出的。鉴于在一定范围的人群中,虽有“潜在”的“朋友”,但也有“潜在”的“泄密者”,故“求友”要有一“试探”性过程。“试探者”既不约而同地“发出”同样的信息,又不约而同地“接收”到同样的信息,所以他们既是“求友”信息的发布者,又是接收者。事实上,这样给出的“求友”信息像是一道“测试题”,“求友”者既要测试别人,也要被别人测试,故是“相互”测试。譬如,“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此中的“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一段可视为“测试题”,其与前文之“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在形式上是相似的,表述内容则依语境之不同而稍异。值得注意的是,“测试题”是以“言语”形式,似“有口无心”地说出,而对“测试题”的回答不是以言语形式,乃是“心领神会”,故“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通过测试者,遂相与为友。庄子以“生死”议题来“检测”他者,以拣选“同道”之友,颇有戏剧“表演”性,其在形式上对后世佛教禅宗以公案话头之勘验展开师资相授似有某种启发性。
“友”的维持机制:相忘无情
通过“拣选”而“相与为友”,修道者遂建立了“友谊共同体”,而要维持此共同体,亦对“友”提出了极高之心智要求,即所谓“相忘无情”。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吊诡”:既相与为友,念念牵挂,又当相忘无情。对之,必须联系“无待”(无所待)概念来理解。即如庄子所说,“个我”不知“真宰”,不识“道”之造化,待于彼我之分,执于“己”之身份,造生扬己辱人之心,日以心斗。若此,则他人者非友也,而皆为竞争者或可利用者,故“有待”(有所待)之人无“友”。“个我”若达“道通为一”,则会认识到“彼”非“我”之竞争者、被利用者,而实同为“道”之所造化者。在此本源意义上,“彼”“我”实为“友”也。
但是,在现实中,“彼”“我”封界,天人分判,此“本源”共在之“友”的关系遂被遗忘,《大宗师》篇多次以“鱼相忘于江湖”之譬说明此点,比如“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有“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造乎水,人相忘乎道术’”。鱼乃是赖水而存活,在水中自在而不觉他,故“忘之”;无水,则只能“相濡以沫”以求活,然此非根本之策,实苟且一时之术也,故不足依,所以“不如相忘于江湖”。显然,由鱼之“相濡以沫”滋生了“相念”之“情”,然此“情”非是“必要”,而是一种无奈之“剩余物”。同样,“人”之间真正“友”之关系是建立在“相忘于道术”基础上,不“念”其友,才真为其友。
从根本上来讲,庄子之“相忘”是一种精神修炼技术,其将对“己”的“无己”(丧我)扩展到“己”“人”彼此之间的“相忘”,要求个体由“有意识”的活动方式向“自发”的活动方式转化,即毕来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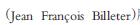 所谓“从低级机制向高级机制的过渡当中,意识会消失,或是部分地消失,或是改变功能,或是发生变化”。故在“友”之生死大化之际,庄子一派的态度是达观的,不持俗世执守存念之心,相反倒是要坚持对“道”之造化的依从,比如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为“友”,子舆示疾,子祀探疾,二人仍是在依“道”而言。子舆自我调侃,“伟哉,夫造物者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不示哀伤而以验其临化之心境:“汝恶之乎?”对曰:“亡,予何恶也……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吾又何恶焉?”其实,“相忘于道术”是一高难度之技术,要求友人之间同时“忘”,若一者忘之,一者不忘,则不成“相忘”。一者不忘,即显“有待”之“心”,嗜欲、犹豫、相信、偏执等种种“认知”(心想)情态有相应之“貌象”显示,“个我”显此“貌象”即露破绽,其虽稍纵即逝,旋为对方所捕捉,此即为他人所看轻而“受辱”,或自感有慊,心生愧意,不能与友比肩。故“友”者,互重而不辱也,因不能忘而“不自重”,即成“受辱”之情势,“友”之联盟即告瓦解。
所谓“从低级机制向高级机制的过渡当中,意识会消失,或是部分地消失,或是改变功能,或是发生变化”。故在“友”之生死大化之际,庄子一派的态度是达观的,不持俗世执守存念之心,相反倒是要坚持对“道”之造化的依从,比如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为“友”,子舆示疾,子祀探疾,二人仍是在依“道”而言。子舆自我调侃,“伟哉,夫造物者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不示哀伤而以验其临化之心境:“汝恶之乎?”对曰:“亡,予何恶也……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吾又何恶焉?”其实,“相忘于道术”是一高难度之技术,要求友人之间同时“忘”,若一者忘之,一者不忘,则不成“相忘”。一者不忘,即显“有待”之“心”,嗜欲、犹豫、相信、偏执等种种“认知”(心想)情态有相应之“貌象”显示,“个我”显此“貌象”即露破绽,其虽稍纵即逝,旋为对方所捕捉,此即为他人所看轻而“受辱”,或自感有慊,心生愧意,不能与友比肩。故“友”者,互重而不辱也,因不能忘而“不自重”,即成“受辱”之情势,“友”之联盟即告瓦解。
“相与为友”的同时又“相忘而游”,庄子给出了一个吊诡的“友谊共同体”。虽然这一“理想模型”就像庄子所描绘的“藐姑射之山”,于现实之人似乎不近人情而不可理喻,然其并非不可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于少数心智能力极高之个体(所谓“至人”)间达致。由此也就引出这样一个推论:庄子的“至人无己”不是可以单独实现的,也非是一孤立状态,“至人”要求于“己”而“无己”,于“人”而“相忘”,故“友谊”于“至人”不是外在之“消费”资源,而是内在“必须”之自我修炼。由此,对庄子一派来说,维持“友”之共同体要求个体自我一生的“依道”而“行”,此非“世俗”之“道德”所能范围,而需要更高的“道德技艺”。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