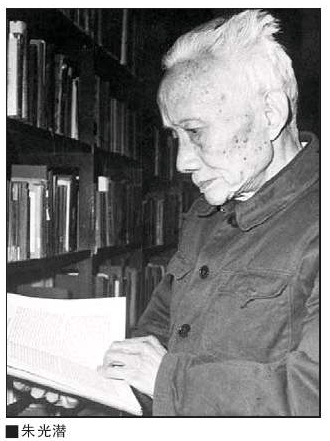
“美是主客观统一”,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不断有新内容充实的命题,展现了朱光潜努力突破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寻求在中国“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框架下,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及西方美学一切积极成果,熔铸新型美学系统的艰辛过程。
朱光潜有“中国美学之父”之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在朱光潜之前,中国尚未出现一个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体系化的美学系统,那么,朱光潜则以“美是主客观统一”为核心命题,以美感经验分析为起点,逐步突破认识论的局限,使美学研究走向实践的历史领域,并且结构化、体系化为完整的开放式体系。
朱光潜美学可以方便地概括为“美是主客观统一”这一命题。从其早期“美既不在心,也不在物,而是心与物媾合的结果”这一观点,到后期“美是主客观统一”这一提法,其间有不可割断的思想联系。“美是主客观统一”,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不断有新内容充实的命题,其内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以及80年代有明显的不同,展现了朱光潜努力突破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寻求在中国“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框架下,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及西方美学一切积极成果,熔铸新型美学系统的艰辛过程。
三四十年代的美在关系说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其准确含义应是“美在关系”说,重点在“统一”(同一)上,而不在所谓“心”(主观)和“物”(客观)上。《文艺心理学》第一章开宗明义,说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人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而非对美的本体论追问:“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朱光潜主张以美感经验的分析为探索“美”的核心,这表明他当时已把握到了正在兴起的“反形上学”的浪潮。
这一时期,朱光潜这一核心命题,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美是主(心)和客(物)统一的一个“结果”,该结果也可用“恰好”(同一)或朱光潜《诗论》中的“境界”概念来表示。这种美感经验所蕴育的“美”,是一种消融主(心)和客(物)之分的生成性的东西,即康德所说的“调节性”的,而非“构成性”的。
其二,“见”即“直觉”,“所见”到的意象恰好传达出一种情趣。“见”(直觉)并无唯心唯物的侧重,朱光潜甚至将之与中国传统的“参天地之化育”思想联系起来,可见其美的定义带有很浓重的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意味。
其三,“美”是一个形容词,所形容的对象,不是作为名词的“心”和“物”,而是由动词转为名词的“表现”、“创造”。
由此可见,朱光潜二三十年代所谓“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虽总体上仍处于认识论背景的大框架下,但已明显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实体化思维模式,他强调的是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同一”,是主客契合的那点“恰好”的快感。
五六十年代的实践美学观
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由批评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开始的,其最大特点之一是受苏联影响,强调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础,而这个基础不容置疑地成为美学大讨论的前提,给美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混乱。
朱光潜要维护他的美非实体化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得不和那些受实体化思维影响很深的美学观点作斗争。朱光潜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主观和客观是相对的,还指出客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甚至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是可以转化的。
由此可见,在朱光潜看来,那种实体化思维以及局限于认识论范围,形而上学化(即一种机械的实体化思维)的思维方式通通应被扬弃掉,由此,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实际上也不复存在了。早期朱光潜把重点放在“关系”上,即消解了物我之分别而达到的物我同一上,现在,他感到这个“关系”还是一种静态直观的看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他认为,在“实践”的观点,特别是“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给美学研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此前,朱光潜还郑重地提出了美学到底能不能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对美学是根本性的问题:应不应该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从1750年德国学者鲍姆嘉通把美学(Aesthetik)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起,经过康德、黑格尔、克罗齐诸人一直到现在,都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一般只从反映观点看文艺的美学家们也还是只把美学当作一种认识论。这不能说不是唯心学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须经重新审定的概念。”
八十年代对实践美学的深化
80年代,朱光潜对“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又做了深入和发展。
突破囿于认识论的主客二元思维模式,自然就要深入到道德、社会历史等诸多领域。朱光潜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论“劳动”的部分,乃至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等著作提供了解放的方向,即从实践的观点看,文艺活动也还是一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本一致性”。在这种生产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包括调动人的“视、听、嗅、味、触、思维、观照、情感、意志、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所有的全部器官,以及在形式上直接属于器官的一类的那些器官”去“占有和掌管人的世界”。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由此,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是它的范围已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包括了人类社会历史诸多领域。二是他所谓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过去直观意义下,只是突出视觉入口的那个“心”(主观)和“物”(客观)的关系问题,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实践着的人。三是由过去“心”(主)与“物”(客)的关系转换成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关系。
朱光潜晚年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翻译和详述维柯的《新科学》?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朱光潜将维柯的“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命题,以及他早年的心物交感的移情说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和系统。换言之,从认识论的个体思维(直观)转到对人类社会历史诸多领域的实践活动(知与行统一的整体思维)。这不就是把过去静观求真的方式,转变成指向未来的动态辩证(知与行)发展的观点吗?如此来看,过去学术界指责朱光潜把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混淆了,以及他没有分清楚艺术生产根本上是物质性生产而非精神性生产,这种种批评便不攻自破。因为,在朱光潜看来,知与行是不能分开的,精神与物质也是不能分开的。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仅仅看做人与自然的物质实践的构成关系是不全面的,它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精神实践的构成关系。
由此可见,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在后期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而非五六十年代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朱光潜的美学可以被称为以历史实践为背景的“同一”说。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