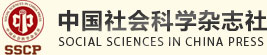西方学术话语下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被看作一门古老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种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传统。我认为,这个定义不切合中国历史经验,或者说不能用来统摄中国博物学。因为说到底,它仍然认为,博物学是一门科学,是以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野对它进行界定,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博物学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

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博物学传统
我坚持认为,传统中国博物学在学术源流和价值取向上,与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所著《博物志》又译《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虽有交涉,内涵却不尽相同。至于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逐步确立主导地位时代的natural history,更有着本质区别。前一定义仍然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下思考,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历史经验套用中国传统,我们应该跳出这一桎梏,建立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自立的学术话语体系。
作为传统社会中“观察世界方式”的博物学,在现代科学建立以后,往往被看作前科学时代粗糙知识和技能的杂烩,或者被偏狭地认为,仅是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趣味杂学。而这一涵括地理山水、人民物产、异国殊俗、鸟兽虫鱼、物性物理、药论药术、方士服食、礼乐文籍、服饰器物,乃至道德人伦、杂史异闻的集合,实际上是关于世界体认的基本思维方式,藉由博物学著作,与字书、医方、类书、杂抄等周边文献及人际传播等方式,扩散、沉淀而为“常识”、“异闻”,且为文人雅士和一般民众所津津乐道。
在我看来,中国博物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和体认世界的基本范式。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不在“物”,而是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直面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因此,博物学不等于“物质文化研究”,更不是什么新的“拜物教”。
建立东亚古代博物学整体框架
中国博物学研究的当下任务,应当整理出版代表性典籍,并对周边文献展开全面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东亚古代博物学的整体解释性框架,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东西知识传统比较范式的新探索。
博物学的知识传统,由中国而渐及韩国、日本、越南,在整个东亚文化圈融汇交织。尤其日本平安后期以降,产生了大量本国学者受中国博物学激发而自撰的纂集、训注和创制著作,对日本文化性格的形成发挥了积极影响。考察博物学在东亚的传播、衍变及其影响,对探索多面的东方思想世界极具价值。我一直呼吁建立东方博物学文献数据库。一方面,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典籍宝藏的重聚;另一方面,厘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古代博物学传统的内在理路。循东方知识传统的脉络,重新审视以近现代科学体系为基石的现代文明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对当下文明困境展开再检讨,并做出回应。
我认为,中国博物学有独特的发端和兴起背景,有自身学术脉络的体认传统,应该建立本土理论框架以及有关史料处理的方法。
中西博物学比较
从整体上看,博物学的兴衰、转承、起复均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代中国博物学“学与术”的背景和源流与西方有很大不同。
古代中国博物学的滥觞可追溯至战国中晚期,这是中国思想勃发的“轴心时代”。博物学是这一学术洪流中的一环,与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农家、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中国博物学兴起的背景较为复杂:一方面,与早期方术传统有较深渊源;另一方面,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扩展,中国对于天下的看法不断丰富,介于想象与真实之间世界图景的“幻替”,构成了地理博物传统。西方博物学通常追溯至老普林尼的作品,并以此视为博物学建立的标志。它与中国博物学的共通点在于,均包含对当时世界图景的理解,而中国传统博物学方术气和人文气更为浓厚,这大概是中西方世界在博物学学术背景上存在的主要差异。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对南方和海外开发、探索规模日渐扩大,在世俗层面,人们的眼界有了极大扩展;同时,外来宗教(最重要的是佛教)、观念的传入,对人们的精神、信仰提出新挑战。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博物学在中古时期趁势大兴。唐宋之际,博物学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型,似乎再没有什么不能放入这个篮子里,这时博物学就悄然转到幕后。爰及明清,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撞击,使得原有的认识模型被打破。所谓“格致”、“博物”之学应时而起,尽管这个时代的博物学和唐宋以先的博物学从学术理路、思维基底上来讲不是一物,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应该说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存在价值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引发博物学井喷式发展。新世界的发现之旅,急切召唤人们给万物确立新的坐标系。至18世纪,博物学迈入鼎盛之世。此后,西方博物学为何出现停滞?看来似乎是新事物、新现象涌现得太多太快的缘故,知识和信息迅速进入精确数理时代和大数据时代,作为个体的博物学家不再具有周知一切能力时,博物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自然被抽空。眼下,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认识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自身无法逾越的困境。因而近十年来,中国学界提出复兴和承接博物学传统的命题,包括西方博物学和古代中国博物学。从根本上说,这是重拾体认世界基本方式的努力,或将生发为学术增长点。当代博物学研究的“再出发”,可以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来看待。
学术研究应当具有当下关怀,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博物学的现实功用,我多少有些疑虑。博物学是否有助于救治人类文明的种种现代性弊端?尽管我们希望如此,但不可寄予过高期待。我认为,既可以有纯粹学术研究层面的博物学,也可以有作为知识陶冶情操的公众博物学。可以把博物学理解为“旧学新知”,也不妨把它看作对当下现实社会起纠偏作用的文化传统。从前科学时代中国人观照世界的基本范式来审视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有可能在数理科学思维模式之外,发现和建立新的世界图景,这恐怕是中国博物学最大的存在价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