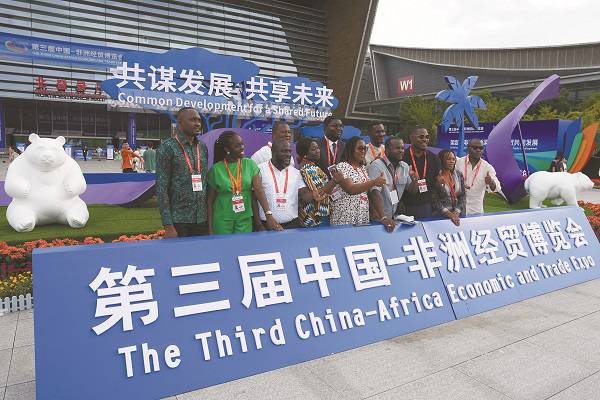“经验”以其超越性的哲学意味,与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存在内在勾连,揭示出新乡土文学创作面向中国经验,描写乡村劳动经验以及由此而生的伦理情感。以何种方式“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这一命题呈现了作家创造性的叙事经验,以及对城乡时空交叠之下乡村日常生活中身体体验的审视,深化并拓宽了“中国经验”的叙事主题,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引发对乡村发展诸多面向的文学省思。
通过劳动经验书写审视乡村伦理演变
乡土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劳动的发生场域离不开广袤的乡村及土地,文学作品对劳动形态的描述、劳动情感的表达、劳动逻辑的揭示往往透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对以“乡村”为写作基点的新乡土文学而言,厚积的乡村劳动经验更是支撑作品乡土价值和理想的精神资源。因此,新乡土文学的劳动经验书写,不仅可以为社会生活及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鲜活可感的文学素材,也能从中窥见劳动群体的精神世界和作家的创作心态。
现代中国文学不乏书写劳动的精品佳作,如写农村土地改革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写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劳动改造的《我的菩提树》《绿化树》,写农村生活变革的《平凡的世界》,写农村劳动形式多元蜕变的《金谷银山》等,这些作品中的“劳动”,时而以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和自由感的精神风貌出现,时而又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异化形态。不管是延安文学所奠定的正面叙述倾向,还是新时期文学对劳动的苦难化表达,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劳动美”和“劳动苦”彼此拉锯的暧昧。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之下,劳动问题凸显了建构新乡土中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贺享雍的《苍凉后土》讲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劳动观念的解放,新一代农民渴望摆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方式,彻底改变过去对于劳动只能依附于土地的单一理解。王跃文的《家山》则将理想社会的劳动生活照进沙湾现实,将农民、土地似血肉般紧紧联系在一起,劳动成了沙湾群众生存繁衍的符码。由于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人们开始逐渐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机械化生产提醒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挖掘劳动伦理赓续与变迁背后内蕴的诸如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演变的合法性依据,积极探求劳动主体背后潜藏的社会实质。
以民族志叙事经验为新山乡巨变存证
张宏森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中提出,“用文学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精神气象”,而乡土文学的民族志叙事经验正好可以为新山乡巨变存证。
首先,志书式的叙事模式有效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和地方志的“述体”体例,这种叙事模式将全景式观察细化到微观事物之中,由“面”及“点”,用事实说话。如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聚焦1589年到1950年之间的“马边”一地,阿来的《瞻对》深描川西的藏族聚居地“铁疙瘩部落”,贺享雍的《乡村志》详细描绘了家乡賨人故里渠县的风貌。这些作品均聚焦于“点”,实际上发挥了故乡这一枚“小小的邮票”的放大作用,如何由“点”辐射整个中华大地,使文学的“当下”与“历史”实现隔空对话,也许可以再一次向“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高密东北乡”“湘西世界”等原乡地标看齐。在文本叙事结构的设计上,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从疆域、语言、风俗等方面全方位挖掘“汤厝”一地的微观历史,不仅呈现了当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也为书写“新史诗”提供了崭新的体例范式,以超越性的叙事姿态而非单一的民间立场为乡村史、农民史和时代史作“注”。
其次,地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故在文学转译过程中涉及对基层治理的书写,不论是表现乡村治理中的实践经验,还是构建乡村善治的文学愿景,民族志叙事都可以为乡村决策者带来启发。作家通过对事例的编织和罗列,使作品的借鉴意义溢出文学的审美边界,特别是在对脱贫攻坚战的书写中,文学对扶贫前线火热的实录以及对乡村新貌的深描,在对脱贫攻坚成绩深情礼赞的同时,也提供了地方性的治理智慧和经验反思。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史诗性地记录了中国的扶贫壮举,作者关注民间,对贫苦农民的生活困境寄予满腔同情,该作品展示出了脱贫攻坚的川渝智慧:脱贫致富的外在显现过程,也是贫困农民弱者心态的祛除过程。类似的作品还有聂鑫森的《驱贫赋》、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唐俊高的《一湖丘壑》等,这些作品聚焦贫困但不囿于贫困,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旧弊新颜都做出了细腻勾画。当然,文学地方志对基层治理经验的书写也需要警惕经验的现实性对文学审美性的挤压,如何平衡这种叙事立场,也是新乡土写作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检索近年来在民族志叙事经验推动下创作的新乡土文学作品,不难发现,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辩驳一直存在于新乡土写作之中,突出表现为这些作品对“乡村寓言”的建构与反向建构。比如,许多作家都冀望以“多卷本”的形式来全景式书写一定时间跨度内波澜诡谲的乡村历史,如关仁山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其中《日头》便试图以“金权汪杜”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代际纠葛和关系图谱为缩影来概括当代中国的乡村文明史,其家族史的书写方式有陷入制造“乡村寓言”幻象的苗头,魔幻的故事及其象征性追求穿插在小说叙事中,使乡村成了小说寓言的演绎场所。
通过身体经验书写聚焦流动的乡村生活
新乡土写作是对变动不居的乡村生活的文学记忆,负载着社会文化批评的历史意义。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如何以一种审美的眼光进入乡村的“生活世界”,“身体”作为感知生活的密钥,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观测视角和言说途径。
新时期以来的身体书写沿着世俗化的路径,出现了“形而下”的叙事倾向。例如,贾平凹的《高老庄》以对身体的病态书写来隐喻乡村生命力的萎缩,韩少功的《爸爸爸》描绘了丙崽身体的残缺与病弱。也有一些作家侧重通过身体本身的遭际与体验来体察流变的生活经验。贺享雍在《土地神》《猴戏》等作品中,创新性地将身体语言作为民间生活情趣表达的重要指标,将身体还原为动物式的存在,以此隐喻乡村内部出现的竞争逻辑。当身体沉潜于生活实践,日常生活经验内部微妙繁复的生命镜像就要求作家们不能再对“身体”作简单的隐喻处理,而必须摘去负累在身体之上的种种神性之光,还原出实实在在的日常身体本真,才能体察生活的丰饶和生命的微妙。
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新乡土写作的言说背景和生成语境,这使得作家们对乡村的思考与观察无法回避“现代性”的渗透,然而“现代性”对文学创作来说却是一个抽象而又难以“及物”的主题,在不得不说而又力有不逮的写作困境下,经验于“身体”之上的现代性体验成为勘探“现代性”最为“及物”的一个落脚点。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农民群体对现代性的体验,更多的是在以城市作为镜像进行自我观照的情境下产生的,在与城市文明的颉颃中建构乡村文明,这种叙事逻辑对新乡土文学创作来说,依然可资借鉴。但更重要的是,新乡土写作要自觉勘探出在城乡文化时空交叠之下,具有自为性的身体面对城市文明的侵袭所做出的生存选择,以及在这一系列自选动作背后差异化的身体体验。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