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研究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图像、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文献学是所有这些研究领域的基础学科,而印度语原典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佛教传入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代译师和求法僧前赴后继,将数量庞大的印度语佛典转译成汉语、藏语以及其他一些民族语言,流传下来蔚为大观的译本体系。这些译本的积累造就了中国本土语境下的佛教体系,由此佛教文化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在这些译典的背后,链接着一个原典的层面。
佛教自公元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次大陆,至公元13世纪初在其主场退出历史舞台。其间,佛陀语录在僧团各派之中由口头流传到结集写定,再到大范围流布,同时也创作产出了大量多种题材的佛教文献,造就了复杂多样的佛教原典面貌。
流传至今的佛教原典所使用的语言,除了我们熟知的梵语、混合梵语,还有流行于印度各地的俗语。这些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雅利安语支。据研究推测,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生活在欧洲黑海和里海之间南俄草原一带先民所操的语言为原始印欧语,其后数千年中这一语言沿着东西两大方向迁徙发展,向西的一支演化出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欧洲的大部分语言;东支则进入伊朗,并进一步东进,于约公元前1500年在印度发展成为梵语,借由《吠陀》经典的传诵保存下来,也称吠陀梵语,是现存的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吠陀梵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古典梵语,成为印度知识阶层通用的“雅语”,也就是现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梵语。在中古时期,印度各地又演化出多种方言俗语,譬如佛教经典所用的巴利语和犍陀罗语就属于俗语的范畴。
佛教属于与主流婆罗门教相对抗的沙门思潮阵营。诞生之初,为了区别于婆罗门教的梵语经典体系,佛教主要使用俗语传述和记录经典。数个世纪之后,随着佛教社会地位的上升,一些部派以及大乘佛教开始转而采用混合梵语(掺有俗语语法成分的梵语)和古典梵语来记录经典,大批佛教论师也以古典梵语这种“学术语言”来著书立说。
印度最初没有纸,书写材质多为棕榈树叶,顺叶脉将叶片裁切为长条形,横向墨书或铁笔刻写,叶面打孔穿绳以捆束,两边可置夹板,称为“梵夹”。在西北部不生长棕榈树的地区,也常以桦树皮为书写材质,桦树皮质地更为柔软,其写本形制初为卷筒,后来也模仿棕榈叶的长条形制。甚至在纸张传入之后,印度的纸质写本也仍然因循梵夹形制。汉语世界将这种形制的佛典写本统称为“贝叶经”。“贝叶”全称“贝多罗叶”,是梵语pattra(叶、文书)一词音译与意译的合体。浩如烟海的佛教原典即是以这种贝叶经的形式流传下来。
巴利语佛典
佛教盛极之时可与婆罗门教分庭抗礼,但终趋衰落并于13世纪消亡于印度次大陆之上,佛教经典随之遭遇了灭顶之灾,而这其中却有一个幸运的例外。锡兰上座部所传的巴利语三藏,取道印度次大陆旁边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传到东南亚地区,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巴利语系佛教也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仍在以原语传承的佛教形态。
巴利语(Pali)是印度中古俗语的一种,据上座部自传,巴利三藏成于佛教首次结集,所用的语言就是佛陀的母语,即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然而学术界大多认为,巴利语很可能是基于西部方言的一种文献语,巴利语佛经也并非全数形成于初次结集。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巴利语佛典,也包括下面要提到的犍陀罗语佛典,是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佛陀言教的最早传述,而其中巴利语文献的规模最大,故历来为佛教研究与实践者所重。
印度语言均以记音文字来书写,同一种语言可以在多种不同文字之间“等价转换”。在佛教南传的过程中,巴利语曾被用僧伽罗文、缅甸文、高棉文、泰文等多种字母所记写,而没有专属的书体,近代以来以拉丁字母转写最为通行。1881年创立于伦敦的巴利圣典学会经过百年努力,基于巴利语贝叶经完成了巴利三藏的拉丁转写文本校勘。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译自巴利语的佛典。2009年,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与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Dhammakāya University)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启动北大—法胜巴利佛典汉译项目,开启了我国对巴利佛典的系统汉译,目前已经出版了《长部》和《中部》。
其他俗语佛典
巴利语佛典之外,其他语种的佛教写本就没有了这种幸运,在印度本土几乎消失殆尽。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在印度文化圈的边缘地带搜寻写本遗踪,致力于恢复重建佛教原语文本体系,其间的新发现不断刷新着现代人的认知。
一百多年前,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我国新疆地区陆续出土了以佉卢虱底文字(Kharosthi,简称“佉卢文”)抄写于桦树皮之上的佛典写卷残篇,学者破译了这种绝迹千年的语言文字,发现这是一种西北印度俗语,以其中心位于犍陀罗(Gandha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而将之命名为犍陀罗语(Gandhari)。犍陀罗曾是佛教学术重镇,产生过深受希腊风格影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语写本中有法藏部所传的小乘经典,也有初期大乘经典,其抄写年代最早者约为公元1世纪,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佛典写本原件。
就在十几年前,我们对早期佛典的认识又一次被更新。有一批西北印度正量部所传的俗语写本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语言被命名为“信度语”(Saindhavi),其文字书写特征鲜明,称为“信度文”,又称“箭头体”。这是当前佛教学界一个热点,相关研究仍在推进之中。
梵语佛典
上述除了巴利语三藏,其他几种俗语佛典的存世数量都很稀少。而在佛教原典中占比最大的,同时也与我国汉译和藏译佛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梵语佛典,这也是近代学术界重建佛教原典事业中最有成效的一部分。
梵语是印度古典文明的主要载体,有大量文学、哲学、宗教、社会甚至医方、天文、数学、音乐等领域的古代梵语典籍流传至今。然而由于佛教的消亡,在印度本土已经很难寻获佛教的梵语写本。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的周边地区以及我国的新疆和西藏地区都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梵语写本,一次次在国际学界掀起研究热潮,为佛教学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写本研究潮流之中鲜有国人身影,这与逾两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以及我国巨量的写本收藏显得极不相称。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梵文写本研究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令国际瞩目的学术成果。
目前存世的梵语佛典写本,亦即“梵文贝叶经”,主要有尼泊尔、中亚以及我国新疆、西藏四大来源,历史上汉地也曾大量输入梵本,但遗憾的是这些写本几乎全部失传。
尼泊尔所保存的佛教梵文写本,构成了现存梵语佛典的主体。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梵语佛教写本,20世纪70年代,德国与尼泊尔合作开展写本的拍照、整理、编目工作,共拍摄整理文献18万余部,其照片目前已向国际学者开放。除梵文佛典以外,这些写本还包含了大量非佛教文献以及尼泊尔语、印地语、藏语等非梵语文献。这些文献的抄出年代相对较晚,一般不早于9世纪,大多是12世纪以后。
中亚地区出土的梵语写本年代则比较早,但数量远逊于尼泊尔写本。这部分写本主要出自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即“犍陀罗文化圈”。20世纪30年代,在巴属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一个佛塔内发现了上百部写于6—9世纪的佛教梵语写本,其中的大多数现已刊布照片或校勘本。阿富汗地区出土的梵语残片较为零碎,但抄写年代较早,最早有2、3世纪之物,主要收于挪威的邵格延藏品,近年来也已陆续刊布。数年前在阿富汗的梅斯·艾娜克新出土了数百叶约7世纪的梵文写本,我国学术界对此的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之中。
我国新疆地区在古代曾是佛教兴盛的区域,沙海之下埋藏着大量佛典遗存。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列强的探险队在新疆攫取了大量梵语写本,以残叶断片为主,完整者少,多抄于6—8世纪,现分藏于英、法、德、俄、日等国,其中多数已对学界公布。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地区仍陆续有梵本残叶出土,主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
我国西藏地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座有待开发的梵本宝库。对于那些尚未发现梵文原本的佛教文献,这里是最后的希望所在,因而极受关注。西藏所藏的梵文贝叶经抄写年代相对较晚,多为10—13世纪,但其部头大而且保存完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学僧罗睺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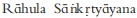 ,1893—1963)与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曾分别造访西藏,在夏鲁寺、俄尔寺、萨迦寺等处发现了大量梵本,他们带回的写本照片掀起了国际学界的梵本研究热潮,在此基础上出版的校勘本达数十种之多。
,1893—1963)与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曾分别造访西藏,在夏鲁寺、俄尔寺、萨迦寺等处发现了大量梵本,他们带回的写本照片掀起了国际学界的梵本研究热潮,在此基础上出版的校勘本达数十种之多。
我国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系统调研存于西藏的梵文贝叶经。1961年,布达拉宫所藏梵文写本之中的259函被征调至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这些写本中的大部分原藏于夏鲁寺。王森先生为这批写本编制了简目。1993年这批写本被运回西藏,现存于拉萨的西藏博物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存有这批写本的缩微胶卷,以之为基础已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另一部分的西藏梵文贝叶经则一直存留于西藏各个寺院。1983年罗炤先生(1943— )赴西藏对这些写本进行调查编目,至1985年完成四部目录手稿,共载写本600余函,数量庞大,且其中绝大多数是首次发现和披露。罗炤目录传到西方学界后,引起极大关注。从2005年开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展开合作勘校这些写本资料,至今已出版研究专著二十多种。200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专门成立了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多年的普查摸底、编目影印,到2011年3月,影印了西藏各地收藏的几乎所有的梵文贝叶经,印制了61册的《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未公开)。2013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成立,从2014年开始出版《西藏贝叶经研究》期刊,陆续发表了一批写本研究成果。
佛教研究中有巴利语大藏经、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文献集成的概念,却从来没有“梵语大藏经”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断被更新续写的书目,记录着某位学者发现了某部经典的梵文贝叶经,又于何年何处校勘发表。经过数代学人的研究接力,佛教梵语原典的文本体系已经在很大比例上得以恢复,使得众多有关佛教文献史、思想史的研究得以追本溯源,不至于受译语隔膜之困。
贝叶经研究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寻获写本要付出巨大努力,校勘整理过程中还要克服残损、抄误、字体差异甚至照片模糊等种种困难,遇到无头尾无题名的残本,还要比对大量文献以确定其内容归属。而这项工作的意义则是无可替代的,每当一部新写本被转写、整理、校勘、发表,就是一部久佚的先哲著作原文回归人类的共同记忆;而每一部原典文献的回归,都会为多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支撑点和生发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