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我们说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学进入中国的肇始,但国际法知识传入中国,比法学其他知识更早。中国对西方法学的需要,首先是对国际法的需要。那么国际法率先舶来的直接动因是什么?答案是——外交。
1840年国门被打开后,列强在外交中运用国际法和商法,时而作依据,时而当幌子。清廷及其官员还不知外交为何物。没有知识准备而突然遭遇西方,从盲目自信到盲目拒斥再到盲目畏恐。时人以中文“交涉”一词来代表外交事务,不知起于何时。目前资料表明,1875年上海《申报》已使用“交涉”一词(《西报论中日交涉事》,载《申报》1879年6月20日)。《官场现形记》第九回曾云:“不与洋人交涉,宦途甚觉顺利。”日本最早的外交职位设立于1845年(日本弘化二年),大清于1861年3月1日(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才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外交专门人才奇缺,只有一个人算得上堪担大清外交大任者,他就是蒲安臣。他“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大清帝国便于同治六年(1867年)11月任命他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中国教会新报》1870年第86期)。这个蒲安臣是个律师出身的美国外交官,是林肯总统任命的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他居然被中国政府任命,让他在外交中为中国代言,原因就是只有他懂国际法。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国际法”一词,至1873年,还是日本学者箕作麟祥(1846—1897)把International Law用中文转译成“国际法”。可是晚清中国官员大多不知国际法为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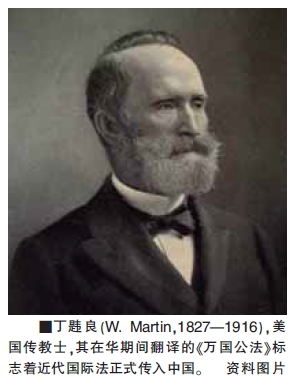
在中国居住并工作62个年头(1850—1916)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4年起在中国“传”起国际法的“教”。他运用中国知识人常有的“附会论”方法,把美国学者惠顿的《国际法的要素》(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与儒家经书进行“附会”,以说服中国人——“万国公法”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1867年丁韪良被聘为京师同文馆教师,讲授《万国公法》。至1879 年,同文馆学生参加公法学大考者有9名,1888年8名,1893年12名。这是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天下”观念。恭亲王在为此上书请求允许刊印出版的奏折中提到,在对外交涉时“彼此互相非毁之际”,才知有此书。他认为洋人和我们打交道都“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和书籍,“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七)。这道出了官方急需国际法的原委,也说明了《万国公法》得以出版的初衷——作为外交中“攻击对方的手段”。恭亲王对国际法的理解只停留在“交涉”与“算计”的工具意识上(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读懂西方、读懂世界的人,才会懂国际法的意义。薛福成于1889年出使欧洲四国,三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原以为“外洋人性情刚躁,不讲礼义之故。乃至欧洲,与各国外部交接,始知其应付各事,颇有一定准绳”(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他认为,为了促使各国对中国改变态度,首先有必要自己改变态度——“凡两国交涉之事,条约所及者,依约而行。条约所不及者,据理而断”(《筹洋刍议·利权二》)。1894年薛福成上奏称,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应“宜识形势、揣事情、谙公法、究约章”(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公法”即国际公法。恭亲王和薛福成都主张外交官要从学习掌握万国公法开始。但恭亲王把万国公法当作攻击和“算计”对方的武器,而薛福成则是把万国公法看作是外交中相互的“信义与契约”,薛氏认为“弄诡辩,曲法”来对待他们,会招致他们的不信任。后来,外国人也发现这一变化,“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上田万年:《关于清国留学生》)。薛氏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湖北官报》1905年第2期)薛福成所批判的,正是清末官员的“中国特色论”,也揭示了中国不用(国际)公法的害处在于不享受公法上的权利。但这样的高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清廷的理解和重视。
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开始传播国际法。比如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从1890年起,主持莲池书院逾10年,其间推行书院课程西学化改革,面向12、13岁的中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其中有“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全通”等;面向16、17岁的大学堂的西学课程中开设“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国律例便览”“海上权力史”等课程。这是最早进行法学知识教授的典例。此外,1897年维新派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也在公法专门学和掌故专门学中,开设“万国公法”。据1898年《湘报》载,唐才常在长沙创办“公法学会”,并制订章程。大约在设立京师大学堂前后,陕西有官员建议本省自设“学律馆”。在当时的建议详文中,驳斥“重视西法以为加于吾道之上”的观点,批评道学与洋务“两相轻而门户分矣”,因而建议“本省自设学律馆”。可见它不只是学习中国律例,而是“兼习章约以识交邻”,实际就是指“条约章程以及时务报章”(《秦中书局汇报》(明道)1898年)。这是地方政府把中学与西学、律学与西法、法律与外交进行结合教育的进步举动。
所谓外交弱国,实际上就是国际规则意识的弱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弱国。制度落后决定挨打的命运。甲午战败令衰老帝国和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远逊于这个近邻岛国。更令国人清醒意识到,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明治维新对日本由弱变强的决定性意义,它也刺激着中国人对待西学重点——西方制度的关注和重视。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修律变法诏书。1902年7月,大清国代表张之洞和英方代表马凯在武昌谈判。7月17日,张之洞通过翻译梁敦彦之口,向马凯传达了一个重要意见:“我们想修订我们的法律,我们即将指派委员研究。您是否同意,在我们法律修改了以后,外国人一律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意味着国际法务与国内变法二者正面的直接关联。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杨廷栋1909年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不同;第二,领事裁判权发生于条约之中,欲去领事裁判权必先改正条约;第三,改正条约必先编订完全无缺之法律”(杨廷栋:《论改正条约与编订法律有连结之关系》,载《外交报》1909年第九卷第23期)。在此他勾勒出了外交与中国法律改良的关系。
随着中国近代知识人睁眼看世界,最后大都把目光聚焦到国际法。因此,学国际法的留洋人数在法科留学生中占比极高。中国逐渐从律学转向法学、旧制转向新制、法统转向法治,外交需要国际法是中国产生近代法律的最初动力。国际法的需求,也是中国律学转型、西法勃兴、法学近代化的动因和契机。说到涉外法治人才,如果以史为鉴,可以从近代找到许多成功典范——法科外交官就有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周鲠生、王世杰、徐谟等。话说回来,没有法科背景的人,其实也并非不能胜任外交官。比如张彭春,因学贯中西,懂中国又懂世界,因此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注入中国儒家“仁”的思想。单凭中国人的智慧,只要懂世界、知文明,即便不懂西法,也不会以“交涉”式的低端心态和方式去搞外交。中华文明藏在中国的“礼”,西方文明大都藏在他们的“法”,文明之玄机奥妙往往藏在国际规则之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