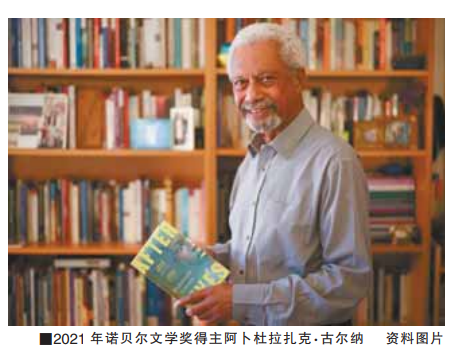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英国的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称他“毫不妥协而且富有同情心地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不同文化和大陆鸿沟之间难民的命运”。选择这位小说家的背后,是近年欧洲的难民危机。
颁奖词里的“难民”困扰
英语原文的“影响”一词选用的是较为中性的“effects”,“鸿沟”是“gulf”(也可以译成“深渊”或“裂口”,指不同文化、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别),“难民”则是“refugees”。最近几年难民问题让欧洲一些国家极为棘手:青壮年劳动力是急需的,可是安置难民开支巨大,即便愿意接纳,要让他们充分融入当地社会却难上加难。古尔纳本人也许曾是难民,他的好几部小说都以动荡时期的难民、移民为主角,《海边》(By the Sea, 2001)主人公萨勒·奥马尔自述,他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
但是,难民身份也常被误用、滥用。当上百万的中东“难民”涌向欧洲的时候,数量同样可观的中美洲“难民”也在向北美迈进。欧盟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在各国分摊难民名额时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尴尬的场景,而原先必不可少的审核程序也不得不暂缓实行。电视上很多难民显得身体健康,表情轻松,还带着手机。抵达欧洲时,他们首选目的地是相对而言生活水平较高的德国和北欧,而不是地理位置更近的东南欧国家。难道他们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冒险吗?但是经济移民在欧洲会受到严格审查,而难民的身份就容易得到同情。就在诺奖宣布后没几天,英国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英国下院保守党议员大卫·艾默斯被刺身亡,嫌犯阿里·哈比·阿里来自索马里。难民/移民问题的挑战一时显得更为严峻,英国人及欧洲人也会进一步思考颁奖词里所说的“鸿沟”的现实含义。
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关注用英语创作的古尔纳,笔者也不例外,从未读过他的作品。诺奖评委会宣布结果之前,不少文学爱好者将肯尼亚小说家恩古齐·瓦·提安哥列为热门候选人之一。
古尔纳比提安哥年轻10岁,1948年底出生于非洲大陆东海岸以外的岛国桑给巴尔, 母语是斯瓦希里语,1968年凭有效期为一个月的旅游签证抵达英国。1964年1月桑给巴尔的苏丹王被推翻,桑给巴尔共和国成立,同年与坦噶尼喀共和国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就是二战后非洲大名鼎鼎的左翼政治家尼雷尔。古尔纳一家在桑给巴尔处于何种社会地位,父母教育背景如何,他们怎样看待家乡急剧的社会变革,最近这一个月来还未见媒体谈及。其实这方面的信息对于人们理解颁奖词里的“难民”一词是不可缺少的。
古尔纳到达英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登记修习大学入学考试课程(A-level),后来顺利入读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学院。这一阶段,他护照上想必有了新的身份。年轻的古尔纳长途迁徙,坦桑尼亚和英国天差地别,然而他在学业上却能做到无缝对接,可见他在桑给巴尔的学校所受的英语教育已经给他铺平了留学英国的道路(斯瓦希里语不是古尔纳的写作用语。现在的斯瓦希里语已由欧洲人以拉丁字母改良,还采用了大量外来词)。古尔纳在历史名城坎特伯雷那所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后在英国定居并结婚,长期执教于坎特伯雷市郊的肯特大学(创建于1964年),担任英国文学和后殖民文学教授,才从该校退休不久。他年轻时曾短期南下赴非洲教书,一生里大多数时间是在坎特伯雷度过的,可以说已在英国深深扎下根来。肯特大学另一位著名校友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后殖民三雄”),他在那里读本科,专修英国文学和哲学。古尔纳曾研究提安哥的作品,撰写了后者的名作《一粒麦种》(2002年企鹅版,非洲文学系列)的序言。他还编辑了《剑桥萨尔曼·拉什迪指南》(2007),剑桥这套作家研究指南丛书在我国大学英文系学生中是颇受欢迎的。这仅仅是古尔纳作为学者所做的专业工作的一部分。他和很多英国当代小说家一样,教书之余也从事创作,处女作《忆别》(Memory of Departure)1987年问世时他已年近四十,1994年出版的《天堂》(Paradise)曾进入布克奖短名单。可以说,在今年诺贝尔奖宣布之前,古尔纳在英国是一位普通作家,假如难民问题没有困扰欧洲人的良知,他还会继续自己的平静生活。

坦桑尼亚和后殖民的挑战
大概在1964年或1965年,笔者从一期新出的《集邮》杂志读到了介绍桑给巴尔及坦桑尼亚的文章,印象中桑给巴尔曾被誉为“丁香之国”。坦桑尼亚原称坦噶尼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是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被英国占领,1920年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二战后改为英国托管地,1962年独立,改名坦噶尼喀共和国。1964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后,桑给巴尔保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桑给巴尔文化混杂,2000多年来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奴隶贩卖现象也早已存在。在欧美,名声最大的来自桑给巴尔的移民当数在摇滚乐世界长盛不衰的英国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摩克瑞(1946—1991),他祖上是来自印度的帕西人(与后殖民理论大师霍米·巴巴相同)。我国爱看欧洲足球联赛的球迷一定熟悉他写的歌曲《我们是冠军》。摩克瑞死于绝症(现在已能够治疗),30年后,另一位英籍桑给巴尔人再度使桑给巴尔和坦桑尼亚扬名。遗憾的是,古尔纳会在桑给巴尔(或坦桑尼亚)拥有一批知音吗?
上述事例说明,所谓的“黑非洲”绝不是本质主义者想象中固定不变的。即便是在坦噶尼喀,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也快速改造了当地文化的本来面目。少年尼雷尔上基督教教会学校时受洗,后去乌干达著名的马凯雷雷大学(提安哥是该校英文系毕业生)求学,二战结束那年回国时已改宗天主教,在天主教会办的圣玛丽亚学院教书,1949年又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经济学和历史学,并在英国与来自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商讨民族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还接受了英国费边式非暴力社会主义思想。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时的诸位领导人都有留学欧洲殖民宗主国的经历,英语、法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变成了他们手中争取政治权力的有力工具。后殖民批评理论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佛兰兹·法农(1925—1961)出生于法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马提尼克岛,参加当地法文高中会考后于1946年赴法国读大学,他的反殖民思想形成于法国里昂,最终用法语呈现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欧洲毕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来自殖民地的年轻学生受到熏染也很自然。留学生中有些人在独立后的祖国权重一时,推行的理想主义政策也有料想不到的复杂后果,英籍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对此深有痛感,《河湾》等作品生动刻画了一些“半生不熟的社会”在殖民者离去后面临的窘境。笔者特地在此提及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奈保尔,主要是考虑到古尔纳和奈保尔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十分相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是英联邦国家,奈保尔在首都西班牙港的女王皇家中学毕业后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英国文坛出现一批“愤怒的年轻人”,以约翰·奥斯本、金斯利·艾米斯、哈罗德·品特和约翰·韦恩为代表的作家群体成员是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像奈保尔那样的移民作家也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英国作家的族裔色彩就更加丰富了,《逆写帝国》(1989)和《白色神话》(1990)等著作就描述了原殖民地居民如何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加入创作队伍,赋予当代英语文学全新的景观。在这一作家群体中,古尔纳并不能归入第一梯队,但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猛然将他置于聚光灯下。
来自“帝国”边缘的移民作家何以能走向中心
笔者想借此机会强调,殖民体系瓦解后,原宗主国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还是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英联邦现在还有五十几个成员国,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英联邦运动会依然吸引着成员国最优秀的运动员。殖民者离去后遗留下很多与艰巨的现代化转型不无关联的制度和机构(即英文所说的institutions),其中包括体育、医院和各种教育设施。英联邦成员国学生留学英国可以享受优惠条件,“新兴国家”的年轻学子仍然把留学英美作为首选(原法国殖民地的年轻人则去法国)。尼雷尔生前得了重病,还会去伦敦的医院治疗。在政治层面,赴宗主国求学的经历有可能产生积极效应。印度国父甘地以及后来的尼赫鲁和甘地夫人留学英国,他们反而缔造了印度。印度继承了很多前面说到的英国特有的事物,板球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最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就是一个例证。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笔者无法获知古尔纳从小到大的经历。如果他出生时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那么从他开始接受教育的一刻他就接触英语了,他完全是在英语主导的语境中长大的。笔者前年在深圳买到三本伦敦出版的英国年刊《英联邦和帝国青少年》(Commonwealth and Empire Youth Annual),蓝色硬皮封面,每本都有三四百页,带大量照片和插图,设定的读者应该是英国和英联邦以及英国海外属地的中小学生。文章大都属报告文学,也有纯虚构作品,作者的姓名基本上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但是内容涉及英联邦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的英语文学研究界大概不会有人去留意这类出版物,其实很可惜。笔者除了想问古尔纳年幼时是否见过类似的刊物,还想知道他上的学校使用何种教材以及它们的特点。不过可以猜想,教材大致与大学入学考试配套,英国文学分量较重。
自19世纪以来,英国形成了包容欧洲大陆流亡者、难民的传统,这些人中不乏作家,比如在1900年左右已经确立了小说家地位的约瑟夫·康拉德。20世纪30年代很多犹太人从欧洲大陆到英国避难,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弗洛伊德和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埃利亚斯·卡内蒂,两人都是犹太裔。卡内蒂主要以德语创作,虽系英籍,却被英国文学史排除在外,好在最近出现了一系列他的小说译本。除了古尔纳,目前在英国的少数族裔作家十分活跃,比奈保尔小一辈的本·奥克利来自尼日利亚,他的《饥饿之路》1991年获布克奖,当时作者才32岁。2008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访华,与他同行的英国女作家基兰·德赛(其外婆是德国人)是印度裔,2006年以《继承失落的人》一书获得布克奖。她的母亲阿妮塔·德赛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主修英国文学,后长期居住在英美,也是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小说《白牙》和《论美》的作者扎迪·史密斯才四十多岁,早在21世纪初就被文学刊物《格兰塔》视为英国最出色的青年作家之一,她母亲是牙买加移民。
说到牙买加,还必须承认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包括牙买加)为当代英语文学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2017)出生于英国殖民地圣卢西亚,读中学时就曾发表英语诗歌,1949年得到“殖民地发展与繁荣”的奖学金后入读位于牙买加的西印度大学莫纳校区,主修英国文学。他也是混血(父亲英国人),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但是他所受的教育是英式的。古尔纳、奈保尔和沃尔科特各具个人特色,但是在有一点上他们是相似的:曾经生活在“帝国”的边缘,爱上英国文学并成为当代英语文学多样性的杰出代表。
(作者系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