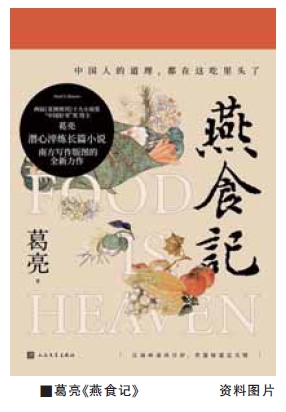
俟《燕食记》发表,葛亮的《中国三部曲》已完成。从2005年在文坛崭露头角以来,葛亮用二十多年的写作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学体系,并独具葛亮气质。这一点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少见的。他的小说以“都市”为中心,既是互文性的,又在一篇篇作品的推进中逐渐明确并强化了写作的方向和意图,且极难得地在当下语境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和文学的余脉。比起前辈作家,葛亮更懂得在读者的接受和作家的自我表达、在历史的“考掘”和现实的叩问中“左右逢源”。
作为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写作
正如接受学理论所指出的,每一个文学文本的生产都暗含着它为其而写的接受者形象,也许作家并不在乎谁来谈他的作品,“但是,作为文本的一个内在结构,某一种类的读者已经被包括在写作活动之内了”。(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由是,“为谁写作”这个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对葛亮来说,这是他创作的中心问题,也是其风格的由来。也许是祖父葛康俞、外祖父等人的传奇人生,以及家族中人辗转流徙的经历,使得葛亮如张爱玲一般,对于“过去”有强烈的“张望”和回溯的愿望。不仅要追溯那停留在血液里的精神文化的传承,还转而扩大到对过去的城市与人、器物与文化历史的“考古”。
福柯以“知识考古学”理论,批评传统史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心与价值中心,力图重估“历史”和“真理”、“权力”和“人”等概念。其中心意义是打破人文研究的线性思维,推翻传统史学所建立的种种连贯、条理分明的历史幻象。由是福柯所呈现的历史是各种事件的排列和叠加,而非前因后果、时空承接的次序书写。这或者与葛亮的小说有不谋而合之处。他的都市写作以城市和家族变迁为主线,却将之潜伏在中外各色人物、士农工商各类阶层的生存状况之中。《朱雀》《北鸢》《燕食记》等长篇小说人物繁多、场景各异,类似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散点透视”的方法,移步见景,以呈现出时代的扰攘嘈杂之声、驳杂缤纷之色。因此,历史隐于市井之中,“知识”在吃饭穿衣之内。可见,葛亮与福柯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相信历史的斩钉截铁、脉络分明。风起于青萍之末,葛亮用“青萍之末”来写时代的大起大落。青萍的摇摆聚散并无明确的方向,充满着各种可能和不确定性,因此葛亮笔下的人物命运起伏和城市演变,也往往有因无果、有果无因。但葛亮与福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相信在事件的纷繁复杂中,隐含着历史的回声和倒影。有些割不断的文化脉络和精神余韵,在城市的罅隙里暗暗地生长,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冥冥中似有时代和人的呼喊与回应。葛亮的小说如《七声》《戏年》《燕食记》常以“毛果”自述,这一称谓暗藏玄机。“毛果”的前身是“毛因”,毛果的存在即是要找寻“毛因”,在重重史实的迷雾中追溯和剖析历史和文化的真相,也侧面凸显出作者的写作情结:作为祖辈的葛康俞、陈独秀等一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如旷野中的呼喊,与时代共陨。葛亮力图用文字捡拾起失落的时代与人,回应和承接祖辈未了的人文情怀。正如小说《朱雀》的结尾,“铜屑剥落”,朱雀“一对血红色的眼睛见了天日,放射着璀璨的光”,叙述的真义呈现出来。
因此,葛亮的“知识考古学”写作,在另一层意义上指的是对人文知识、人文经验与人文情怀的考古,它包括三个层面:器物(故物)、人(良工、良厨)、由器物和人共筑的时代精神。“物”贯穿了葛亮写作的始终。正如他在《绘色观》中所说:“很多司空见惯的‘物’也成为表达生命流程的媒介与窥口,担当了少年成长历程中的坐标。”《朱雀》中的朱雀、《北鸢》中的风筝、《燕食记》里的莲蓉包,历经岁月烟尘,谛视重大历史时事,贯穿全文始末。它们既是物是人非的见证者,也是牵连过去与现在的“伏脉”,是民族地域文化的浓缩。除了这些充当小说之眼的故物,葛亮小说处处是充满隐喻色彩的物象。如《朱雀》中的辟邪、半夏等。“辟邪”是南京的Logo。1937年,叶毓芝与芥川在药铺库房苟合时,看见了“辟邪”望着他们的眼睛,那是审视与惩戒的眼;多年后雅可陪许廷迈去南京博物馆,门前伫立的青铜雕塑也是“辟邪”,龙头狮身,雍容自持,不怒自威。叶毓芝在交欢前,用药铡切了库房里的一束半夏。半夏是一种中药植物,花期在农历五六月间,是夏天之半,而此时正是天气由热转冷、由阳转阴的时期,因此古人认为半夏具有“交通阴阳”的作用。小说借此暗示即将到来的情节:《北鸢》中的仁珏、二玉相合为一珏,暗示仁珏是冯明焕和言秋凰的孩子。
考掘的意义在于“钩沉”,即把被湮没不彰或佚失的事物呈现出来。葛亮对“故物”和“良工”的关注进一步发展为对中国“非遗”知识的考察。其早期小说就有传统工艺和工匠的身影,如201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泥人尹》写的就是泥塑艺人的故事。2021年的小说集《瓦猫》聚焦于古籍修复师、理发师及陶艺师的命运。2022年出版的《燕食记》则以四代粤点师傅的人生轨迹讲述粤港故事。当葛亮细致入微地在小说中普及古籍修复、陶艺制作以及粤点、本帮菜的色香味时,无异于在历史之海中打捞为现代生活所忽略的文化“遗珠”。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仅能对传统文化知识拾遗补阙,感受到中华文明厚重精深所带来的心理震动,亦能体味到文化的绵延流转。或者,这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
时代之“均”与人的“七声”
对文化的考掘和打捞并非葛亮小说的唯一目的,那些流逝于时间之海里不可重现的时代,以及由时代而生的不可复制的人,才是小说沉甸甸的部分。葛亮的短篇小说集《七声》有一个作者自序:“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它们湮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侧畔,与我们不离不弃。……‘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凝聚为大的和音。在这和音深处,慢慢浮现出一抹时代的轮廓。这轮廓的根本,叫作民间。”这段话落实了葛亮的民间立场,这一民间立场与葛亮坚持写人的创作态度有关。“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均”为一种古代乐器,“七声”相当于现代乐器中的七种音调。个体的“七声”合成时代的“一均”。大时代与小人物是葛亮城市写作中相辅相成的主题。
在现代小说家中,葛亮承接了张爱玲、白先勇一脉。这一脉又衔接着《金瓶梅》《红楼梦》以来传统小说的底蕴,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兴味、对细节的沉湎,更重要的是对家国历史之外的市井人物的描写。但与前人不同的是,葛亮从未忘记人物是时代中的人,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或上帝手中,而是由历史趋势和文化属性决定的。历史的枝蔓藏于岁月的肌理中,人物隐于时代的褶皱里,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微渺而脆弱。可是即便如此,人也有人的坚守,虽然这坚守最终往往化作时代的悲歌。葛亮笔下的种种“良工”都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然而却是时代的边缘人、孤独落寞的人,其精神散作历史的袅袅余音。这一写作的着力点在葛亮早期小说中就可见端倪。比如《泥人尹》,小说表面上写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手艺和手艺人的没落,内核却是时代裂变下个人的哀戚。《于叔叔传》写的是城市一对普通夫妻的婚姻悲剧。但绝妙之处在于,这出悲剧不只是出于夫妻双方的个性差异,根本原因还在于时代的变动和城市的发展。与时俱进的丈夫与逐渐退伍守旧的妻子,悲剧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葛亮曾在南京、香港、深圳、温哥华等地停留,也曾对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多有描绘。多样文化的成长经历使他能以开放的、世界性的视角去审视人和城。但葛亮之为葛亮的原因在于,在各种文化的交错撞击之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些家学的底子、深厚的传统文化因子。因此,“七声”之中,最强的声调是执着和坚守。这也是葛亮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在这一点上,葛亮与白先勇十分相似。葛亮常以小说中的人名或小说名致敬写作上的前辈,如《不见》中的聂传庆致敬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同名小说《阿霞》致敬屠格涅夫。而葛亮的《安的故事》则令人想起白先勇的《谪仙记》。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也多有十分偏执的人性,很多人物是极端的人。《谪仙记》中的李彤家世显赫,出国留美后,父母意外去世,瞬间成为异乡的漂泊者,于是放逐自我,用轻佻高傲、戏弄人间的姿态游走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安的故事》中的安,是一位优秀的女大学生、出色的学生干部,与黑人Mark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分手,心灵受重创。于是安与李彤一样,玩弄别人也玩弄自我。这两位美丽女性,不甘于命运的摆布,用孤傲、戏弄命运的方式来回击命运的戏弄和生活的钳制。这种“不知所起,却一往而深”的固守是葛亮与白先勇的相通之处。但不同的是,当守而不得,当人与命运的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时,白先勇的人物有更为彻底的决绝姿态,而葛亮笔下的人物在“七声”之中,带着隐忍的精神。
由此看来,白先勇的骨子里还是浪漫主义的,葛亮则是现实主义的。《谪仙记》《安的故事》的不同结局就已意味着两者的分野之处。李彤在游戏人间后,自杀身亡。安却在几年后结婚生子,这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无人得知。同样的情节也发生在阿霞身上。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有一部著名小说《阿霞》,少女阿霞以独特勇敢的个性给世人烙下了精灵般的深刻印象。葛亮写了同名小说,小说中的阿霞也与屠氏的阿霞一样,身世独特,有不同于常人的“异质”灵魂,勇敢单纯。但屠氏的阿霞出身于上层贵族,深受哥哥的宠爱。葛氏的阿霞却家境贫寒、身份卑微,有轻微的躁狂抑郁症,还有一个看不起她的吸血弟弟。最后阿霞因为路见不平,帮别人出头而坐牢,出狱后结婚生子,成为一个极普遍极庸俗的乡民。以上诸种比较,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葛亮也继承了张爱玲的观点: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负荷这时代的是大多数软弱的凡人。这些时代里的软弱凡人,既有自己的“负隅顽抗”,也有对命运的顺从和隐忍。
就像我们在张爱玲小说中读到“市声”和“苍凉”,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读到“瞬息繁华”和“无言的痛楚”,我们在葛亮的小说中能读到的是“一均之中,间有七声”,那是时代的巨轮碾过的声音,是隐忍的悲欢,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冷之音。一方面,古典精神丢失,传统文化无奈却又必然的没落;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都市的飞跃发展,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身不由己地陷落在由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文明中,无从摆脱。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