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国庠(1889—1961),出生于广东澄海。曾用笔名有杜守素、林伯修、吴啸仙、林素庵、吴念慈、杜惑、林柏等。
1889—1907年,他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1907—1919年,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1919—1949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和学术研究。1949—1961年,在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工作,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即今华南师范大学)第一任院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兼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等职。

杜国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翻译。20世纪20年代末期,翻译了《辩证唯物论入门》《金融资本论》《史的一元论》《社会学的批判》《普列汉诺夫论》等著作。二是办刊物。20年代,创办《社会问题》杂志,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组织“我们社”。30年代,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主编,参与党的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工作。三是著书立说。杜国庠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论著大多收集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杜国庠文集》《杜国庠选集》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他所处的时代具有开拓和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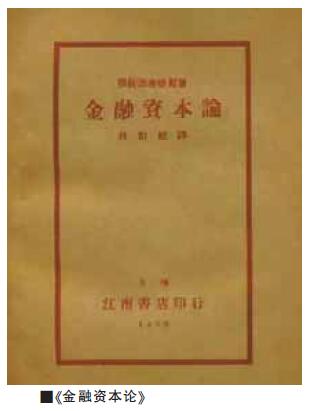

杜国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卓有成效的学者之一。他出生于广东澄海,早年时,近十年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十二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则使他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阐扬中国古代唯物思想、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点的价值等方面,具有开拓和引领作用。郭沫若曾以“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赞扬杜国庠对革命和学术研究的贡献。
党的理论战线上积极的战士
1919年杜国庠从日本学成回国,从教学、组织、宣传等方面投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北京六年,他在所任教和兼职的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唯物辩证法。在住所“赭庐”常与进步青年、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与郭沫若等组成群众团体“孤军社”,并发表文章《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925年,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宣传革命思想。
1928年杜国庠到上海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党的理论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空前尖锐。杜国庠一到上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他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组织“我们社”,在《太阳》《我们》《新流》等刊物发表文章。他撰写的《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批判了一些错误言论,对当时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等哲学著作,这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上海期间,杜国庠还肩负党的重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为把左翼文化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而努力。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委员,积极参与组建左联的筹备工作,并在左联一成立时就加入其中。他发起组织“社会科学者联盟”,参加了社联的党团。此后,为了便于领导,社联与左联、教联、剧联、美联等合组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杜国庠是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其机关刊物《中国文化》的主编,活跃于当时的理论论战。1935年杜国庠被捕,他在狱中与敌人斗争时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37年杜国庠出狱后,就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从事学术研究,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他起初在抗日将领张发奎所属的第八集团军任职,后调入战地服务队任上校总务科科长,继而兼任代理队长,在军队和社会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根据党组织和周恩来的指示,于1938年调到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外宣传处任第一科科长,负责设计和日文翻译。杜国庠和三厅的战友们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拦和破坏,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后来,国民党撤销了三厅,改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企图以这一组织使进步文化人士闭塞言路。杜国庠等文工会委员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开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各种学术活动,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并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杜国庠在这段时间潜心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先秦诸子的研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对各种错误的观点进行批判。他在《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中,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中国古代礼乐的起源、发展和新的前途,批判了为蒋介石制礼作乐的反动意图。他还针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写了许多充满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札记和论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国庠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对澄清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迷雾起了积极作用。1946年他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认真探讨先秦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努力把中国思想史的源头搞清楚,使读者不为“时代落伍者”所蒙蔽。杜国庠还担任过《新思潮》周刊的主编,既正面宣传马列主义,又批判当时理论界存在的错误思想,如发表《思辨篇》批驳了一些混淆视听、阻碍广大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杜国庠致力于文教、社会科学的建设和研究工作,直至1961年逝世。侯外庐在杜国庠逝世后出版的《杜国庠文集》序中这样说:“杜国庠同志始终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积极的战士”,具有“不放松任何机会和敌人斗争的坚强有力的战斗意志”。
运用马克思主义整理研究中国文化遗产
五四运动以后,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批判地继承,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氛围变得十分浓厚。就研究方法来说,当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偏重于文字学、训诂、考证、校勘层面,希望解决儒家经书中的问题;另一种倾向于探讨诸子思想自身,希望从中发掘某些现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触及诸子思想的实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相联系,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构建中国思想史的叙事框架。杜国庠作为理论战线上的战士,服从革命的需要,积极转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为开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侯外庐指出:“杜国庠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有卓越成绩的。”
运用唯物史观解读思想、历史。杜国庠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这种特色贯穿于他的这类著作中。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绪言中,他提到先秦诸子思想“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探讨思想史,这是杜国庠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突破,从而正确说明“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因此,他对于孔子思想,“从孔子所处的社会去找说明”。他认为读墨子的书,“就必须联系着他的社会背景来研究”。他指出荀子处在“社会变革,日近成熟”的时期,所以荀子的思想“便形成了由礼到法的过渡形态”。在《论〈公孙龙子〉》中,他认为公孙龙的思想既继承和发展了学术遗产,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和社会的现实”。在《荀子对诸子的批判》中,他在解释为什么荀子能担起对诸子的总的批判任务时,指出这是因为战国末是奴隶制社会的结束阶段,所以学术思想也到了可以总结的时候。在《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中,他认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礼乐,“其本身实随着时代而发展”,“是适应于奴隶社会后半期到封建社会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东西”。在《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中,他分析了清谈盛行的社会根源。在《范缜的唯物思想》中,他首先研究了《神灭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其问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简言之,杜国庠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来证明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思想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思想发展的规律才能得到正确的揭示。
以唯物辩证法对思想史作动态分析。杜国庠研究中国思想史,不仅重视对思想作唯物史观的解释,而且注重以唯物辩证法分析思想的渊源流变,这种研究方法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尤为明显。他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专著以及《从荀子的〈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荀子对诸子的批判》《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等论文中,对先秦诸子进行了系统而辩证的考察。首先,坚持辩证的发展观,把先秦思想史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过程。他指出,先秦诸子“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这样的批判过程,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诸子以及各家之间的承继关系,从各家思想发展演化过程梳理思想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他认为久已湮没的哲学理论宋尹学派前继儒墨,又对孟子、荀子、庄子乃至惠施有着深刻影响,是先秦思想发展史的关键环节;公孙龙“上承惠施、尹文及其他辩者的遗产,下给荀子、墨家作了准备工夫”。对于思想发展,他进而解释说,“社会不会停顿,思想也就不可能停顿”,“一切‘异端’思想遇到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它就会披着‘正教’的外衣而出现,或者暂时进入伏流的状态,等待着可以让它奔腾澎湃的时机的到来”。其次,把对立统一关系贯彻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杜国庠认为先秦诸子思想“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和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他根据诸子各家思想的实际,辩证地分析并揭示诸子思想之间的矛盾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但彼此依存、相互渗透和转化。如儒墨在天道观、政治、伦理和名辩思想上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因为孔墨“俱道尧舜”,同时墨子“学儒者之业”,针对儒家的礼乐而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可见,杜国庠以唯物辩证法理清了先秦诸子思想发展的线索,从而确认“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发现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这成为杜国庠关于先秦思想发展史独具一格的学术思想。
阐扬中国思想史的唯物主义传统
杜国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坚持从哲学党性原则的高度对思想作路线分析,并阐扬其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批判唯心主义错误,为早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转变为科学的思想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侯外庐说:“杜老研究思想史,上自先秦,下自当代,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始终如一地贯穿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毕生不遗余力地阐扬唯物主义传统,揭露、批判唯心主义错误。”
在比较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释其中的唯物思想。杜国庠分析先秦诸子思想,指出他们在宇宙观和认识论问题上分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他对孟子与荀子、《墨经》作者与公孙龙等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运用这一方法的范例。杜国庠认为,孟子和荀子都接触过宋尹的学说,但孟子受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影响,根据“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把孔子的“性相近”的见解发展为性善说,因而给予仁义礼智“先天的根据”。在认识论上,孟子把宋尹学派的“修心”、养生之术发展为基于性善论的存养(修养)学说,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莫善于寡欲”“外物皆备于我”等思想观点。这表明孟子的哲学倾向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对于荀子,杜国庠认为“荀子的宇宙观(《天论篇》)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富于唯物主义的因素的”。他指出“天论”思想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不再是“西周以来的上帝神的天道观”,也不再是“宋尹学派之类的形而上学的天道观”,而是主张“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从而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神秘天道观。他又指出荀子扬弃了宋尹的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一种能动的矛盾运动过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从而在先秦诸子学说中最近于科学。至于《墨经》作者与公孙龙的思想,杜国庠认为两者是根本相反的。他盛赞墨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出《墨经》作者扬弃墨子“天志”“鬼神”思想,又从“物在知之外,理在物之中”这一根本观点出发,形成唯物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而对于公孙龙的哲学,杜国庠认为,它“是一种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公孙龙不但把所谓的“指”看作可以离开物而独立自藏的东西,而且认为它是离开人们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着的。
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中发掘这一时期的唯物思想。杜国庠批判魏晋南北朝清谈玄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指出“谈士”的宇宙观“总归是趋赴于观念的世界”,人生观上“虽自命为‘风流’”,但不关心世事,为求胜,不问真理所在,是为辩论而辩论。他同时强调,这一时期在玄学氛围的笼罩下,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的唯物思想,并进一步发掘了杨王孙裸葬论、杨泉《物理论》及范缜《神灭论》等唯物思想遗产。在《两千年前杨王孙的裸葬令》中,他认为杨王孙裸葬论的“精神离形,各归其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死者不知”的理论,为范缜的《神灭论》先导。魏晋间的杨泉在《物理论》中曾提出宇宙的一切生于水的观点。对此,杜国庠在《杨泉的水一元论》中赞扬说:“杨泉是一位唯物论者”,“在那崇尚玄虚的环境里,能够‘卓尔不群’,独标唯物见解,真可谓难能而可贵者。”在《范缜的唯物思想》中,他指出范缜《神灭论》在中国唯物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赞扬范缜提出的“形存而神存,形谢而神灭”唯物论观点,对摧毁佛教神学的“神不灭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阐述明清进步思想家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中,杜国庠认为戴震对物我、理事关系方面提出的物在我之外、理在事物之中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唯物的反映论”。在《论“理学”的终结》中,杜国庠对明清之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颜元重致用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黄宗羲否定心学,唯物地解释了理与气的问题;顾炎武是“最重客观事实的人”,具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王夫之在宇宙观方面提出“物生于有,不生于无”这一有别于理学和道家的观点,在道器论上确定的“器在道前”的观点“无疑是光辉的唯物论的理论”;颜元的做人治学富于“实事求是”精神。
发掘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实践观点价值
杜国庠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他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使其在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注重发掘思想所蕴含的实践观点,阐发它们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无论是对先秦诸子思想,还是先秦诸子之后的范缜以及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杜国庠在介绍他们的思想时,都很注意宣传他们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
在先秦诸子研究中,杜国庠指出,诸子“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这就肯定了各家都想以自己的学说去推动或影响当时的社会变革。他对墨家思想实践观点及其思想价值的深入挖掘,体现了这一研究特点。杜国庠认为,墨子很重视实践,且墨子以身作则去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举了墨子为实现其“非攻”的主张,说服楚王,阻止楚国进攻宋国这一历史典故,来说明墨子对实践的重视。杜国庠详细分析了墨子创立的“三表法”。他指出,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指接受古时的经验,这种经验包含过去的“言”和“事”;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要求以民众的经验为根据;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要求从政治实践上检验是否符合国家、百姓和人民的利益,也就是以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他认为,墨子的“三表法”,无论是以经验为立言的标准(第一、二表),还是以实践为理论真伪的检证(第三表),基本上都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以实践精神为基础。杜国庠认为,后期墨家在知识获得的三种方式(闻知、说知、亲知)的理解和认识,在名实关系(用实去正名)等方面,都是在墨子实践精神理解基础上对墨子思想的继承。他还认为,墨家思想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这十项主张,虽各明一义,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简言之,杜国庠对墨家重实践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墨家把重客观贵实践的精神带入认识论,“奠定了以实践为认识真理的标准的墨家唯物认识论的基础”。
在研究范缜的唯物思想时,杜国庠高度赞扬了范缜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从而尖锐地抨击了封建贵族和僧侣地主大力提倡佛教的政策,以及深刻揭露佛教势力恶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的求实精神。在《范缜的唯物思想》中,他详细引录范缜在《神灭论》中揭露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的描述,指出:“《神灭论》的用意在于挽救社会因佛教流行所发生的弊病。”他赞扬范缜“吾哀其弊,思拯其弱”的忧国忧民的历史进步性,说:“真正的思想家,决不能超然世外,对于当世的弊政恶俗熟视而无睹的。”
对于顾炎武,杜国庠指出他做学问的目的是“拨乱涤污”“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的“经世致用”。正因为他志在经世致用,“必须足以见诸行事者方算学问”,所以他做学问的方法是实事求是。杜国庠认为方法是由客观的需要引导出来的,于是引用顾炎武的门人潘来在《日知录》序中所言来评价顾炎武的学术思想,说:顾炎武做学术,“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杜国庠评价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时指出,黄宗羲对君权横暴的指斥,萌芽了民主主义政治思想。至于颜元,杜国庠认为,他把做人治学“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学说体系,形成他的实践主义;他不但以实际的效用去衡量学术的标准,而且他的表现方法也是从寻常日用中采取例证;他既反对以讲读为学问,也反对静坐功夫,主张“动”“习行”,即注重实践,重视效果实用;他一生做事认真踏实,认为读书不应做书呆子,要注重其经世济民的目的,指出“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
总之,杜国庠在党领导下的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不愧为党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一生,永远是后代的典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百年历程和经验研究”(22XDJ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龙岩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