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28日,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同志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表彰。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联合开展,自1999年开始。本届共93位专家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97家单位或团体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表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合理人才梯队,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拓展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空间,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高地建设跃上新台阶。为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本报深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先进集体的突出事迹,敬请关注。

赵汀阳同志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作为无党派人士,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在研究工作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坚定不移地走为人民做学问的道路,善于用学术讲政治。
赵汀阳从事科研工作30多年来,始终坚守学术情怀,对学术孜孜以求,心无旁骛,潜心治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共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1部,外文著作4种8部,合著2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两种权威期刊上合计发表论文33篇,在权威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上跨界发表论文4篇,在西方刊物或文集上发表论文28篇;在其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50篇。
赵汀阳在研究工作中一直保持思想的创造力,造诣很高,在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中做出多项优质理论成果,包括多种具有原创性且居于世界前沿的中国理论,如“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旋涡理论”“预付人权理论”“新金规”“可能性的哲学”“第一个哲学词汇是否定词”等,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国际上亦有较大影响力,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与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合著了Un Dieu ou tous les dieux(法国Cent Mille Milliards出版社2019年出版),与法国哲学家赫吉斯·德布雷合著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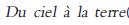 (法国Les Arènes出版社2014年出版)。2019年被法国《新文学杂志》评为“影响世界35个思想家”之一。
(法国Les Arènes出版社2014年出版)。2019年被法国《新文学杂志》评为“影响世界35个思想家”之一。
赵汀阳以其突出的科研业绩和学术贡献,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长城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受邀到国内外多家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兼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常委(Steering member of Transcultura Institut European)、美国博古睿研究院资深研究员(Senior fellow of Berggruen Institute)等。
只要人类存在,智慧之火就永远不会熄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就是这样一位播撒理论火种的劳动者。
1961年,赵汀阳出生在广东汕头,从事哲学研究3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学术情怀,以学术服务人民,提出了“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旋涡理论”等原创理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致知力行,踵事增华。赵汀阳一直保持思想的创造力,以具有未来意义的问题为目标,探索实现中国思想的当代化和世界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多种语言,被认为是“中国学派”代表作。10月28日,赵汀阳荣获“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本报专访了赵汀阳,借此深入了解其哲学思想之路。
做有技术的劳动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老师,您是1961年生人,今年刚好60岁。从事哲学研究30多年来,您始终坚守学术情怀,对学术孜孜以求,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研究心路历程。
赵汀阳:我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值得说,也对“心路”没什么兴趣。很抱歉,实话说,我觉得“心路”这个词汇有些恐怖,刚一想就被吓退了。以前有个采访,也是要讲点个人故事,真的没什么个人化故事,如果有,或许与同时代的人差不多。我只好回答:我是个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干活,我干了一些活,想的就是如何把活儿干好。机器人是个玩笑,认真说,我是个劳动者,想做一个有技术的劳动者。
劳动者的经验很吸引人,你知道吗,是农民第一次创造了“未来”的概念。那是七八千年前,也许更早些,文明的早期,新石器时期,是第一批开始农耕的人。种植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以劳动去预定未来,农民知道秋天的收获是可期的(排除天灾的话),在此,人类通过种植的行为第一次定义了作为人的时间的“未来”。没有可预期的事情就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农业之前,自然时间无所谓未来,只是来回往复的循环过程。甲骨文的“来”字,通常认为其原型就是麦子。麦子就是人预期未来的隐喻。我做哲学,与种麦子的感觉差不多,所以我的经验和农民的经验差不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过程中,哪些理论给了您启迪?让您能够源源不绝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理论的因素有哪些?
赵汀阳:太多的书都对我有启发,多到无法罗列。能够流传下来的书绝大多数都有了不起的思想在里面,都隐含着深刻的问题。我愿意说,“几乎所有名著”都是重要资源——之所以说“几乎”而没有说“全部”,是因为尚未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另外一个经验是,仅限于哲学著作来看,总体上说,二战前的西方著作比二战后的要高明,或许因为二战后的冷战思维和“政治正确”导致思想的藩篱太多。不过在其他领域,比如史学、人类学和博弈论等,却是二战后的更有创见。虽然得以流传的书基本上都是好书,但需要理解的远不止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作者时代的问题处境和思想动力,如何理解作者的解题路径,如何开发其中那些隐藏着的而又能牵动当代问题的能量。这一点对于分析和开发先秦思想尤其重要,因为先秦思想的文本都非常简练,因而问题隐藏得更深。这显然需要方法论。方法多多,我常用的方法论主要来自《周易》《道德经》、维特根斯坦、哥德尔、分析哲学、博弈论还有数学直觉主义等的组合。当然一定还有更好的方法论,只是我还没有学会。我对当代法国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就很有兴趣,它们可以说是一种“多方链接”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我还没学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自己哪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最为满意?请您分享一下“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和“旋涡理论”等这些原创性理论背后的思考故事。
赵汀阳: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也不存在唯一真理,所以每种理论都永远有余地,我这些理论也没有能够达到满意的,都有改进余地。在这些理论之间好像也难以比较,因为针对的问题和领域都不同,缺乏通约标准。你提到的这几个理论,天下体系与亨廷顿问题有关,与全球化状态有关,更与当代新技术发展有关。在亨廷顿之前,我一直以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足够好的,可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却解决不了亨廷顿问题,因此我建构了一个应对亨廷顿问题的天下体系。天下概念来自先秦,但“天下体系”理论针对的是未来世界的问题,不是回答古代问题。共在存在论则几乎是从纯粹分析和推理获得的,存在论和逻辑差不多都不需要历史语境,不过应该有先秦思想的潜意识,因此更容易发现“共在先于存在”的原则。旋涡论就非常语境化了,是从中国历史、考古学和哲学中化出来的。其中,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是利用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多学者的成果;方法论方面,则主要是博弈论和布罗代尔式的中时段和长时段分析。
种出携带能量的观念或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此次获得“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这一表彰?
赵汀阳:除了专业技术,我好像也不会别的,所以觉得很贴切。做技术活儿有实在感,觉得能接触到问题本身。我做的是哲学工作,用的工具是语言、逻辑和文本。语言和文本都包含着以往思想者对历史的感受,对问题的经验,还有重叠的语境,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表达整个生活。因此,使用语言来工作就置身于整个生活的问题之中。复杂性、语境化、历史性是人文学科不得不身处其中的处境,所以,语言和逻辑的“纯粹”技术也必须应对复杂语境,或者说,处理复杂语境本身就是一项技术工作。语言本身的秘密就很多,我看过沈家煊先生的《名词和动词》,很有收获,发现自己其实对母语也没有透彻理解。
感觉上我的工作经验比较接近农民的经验,好好种菜,种出有营养含量的菜,这种经验转换到思想田野,就是种出携带能量的观念或理论。思想田野广阔深厚又复杂,问题无数。我和大家一样,都在其中,各自遭遇面前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您被法国《新文学杂志》评为“影响世界35个思想家”之一,您如何看待国际学界给您的这一评价?
赵汀阳:我不了解这个评价是什么标准。但这个评价说明评价人读过我的书,很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做研究,您平时有哪些爱好?
赵汀阳:做研究就是最大的爱好。偶尔画漫画。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您的研究重点和规划有哪些?
赵汀阳:30年来我一直做形而上学,近年来还有历史哲学,都要接着做的。我跟着问题走,遇到的问题到哪里,我去哪里。
形而上学是永恒问题,就像西西弗斯那块石头,总也不能推到山顶。近年来在研究“本源”问题,主要在寻找一种有效率的溯源方法论,我称之为“溯源递归”,其中包括“溯因推理”的迭代运作,希望能够由此发现哪些问题是哲学的本源问题。一个具体发现是,否定词(不)的发明是人类思想的最大存在论事件,否定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接下来会以溯源递归的方法再做些具体研究。
历史哲学就像历史学一样复杂,虽然可用的资源不少,但问题是,人太复杂,要给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太难了。历史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人类全部事情,不是研究人类生活某个方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相当于全部学科的联合体,属于复杂学科,所以当代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所有方面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难以处理的场面,传统的形而上学善于处理宏大问题,但在处理复杂性的问题上并无优势。人的行为不够稳定,历史事件更缺乏稳定性,对于不确定、不稳定的复杂对象,要找到有效分析的方法论真的很难。简单地说,如何才能有效地理解过去,还缺乏足够有效的方法论。另一个难点是,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就是说,如果历史的目的只不过是知道过去什么样,那历史的意义就很有限,人类对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未来的兴趣,未来才是意义所在,未来预存了无穷的意义。可是,从关于过去的知识无法必然推论未来,这是休谟命题之一。可是除了历史,我们无所凭借去研究未来,那么,历史如何研究未来?也是现在无法解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