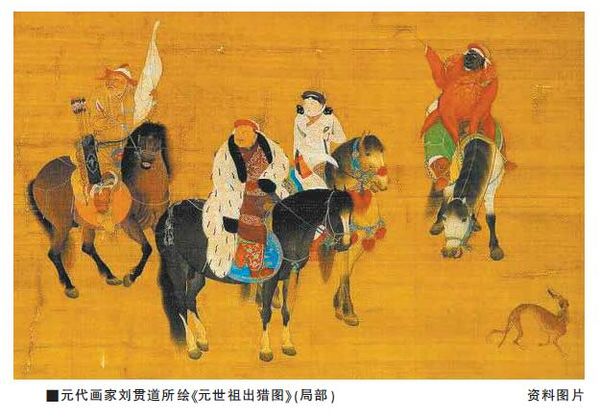
《明史·刑法志》载,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位伊始,即命儒臣日讲《唐律》,意图以《唐律》为圭臬,建立明朝新的律法体系。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终定本完成。《大明律》一改《唐律》十二篇的分类,转向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体系,此种转向受到了《元典章》的影响。明初这种法律演进模式,既体现了中华法系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元明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力量、不同群体之间传承互鉴的结果,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法律演进。
《大札撒》尚处于习惯法阶段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时,庶事草创,唯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刑政,官制简约。据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1226—1282)所述,成吉思汗“依据自己的想法,他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页)。这些被志费尼笼统地称为法令、法律或者刑罚的条文,被后世蒙古史学者称为《成吉思汗法典》或《大札撒》。
这部传说中的法典是否真正存在过,引起了后世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瑞典学者多桑确信其曾经存在,他在19世纪初成书的《蒙古史》中写道:“成吉思汗曾命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尔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此种法规名曰《大法令》,由其后裔保藏之。”(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多桑的观点得到了法国学者格鲁塞、美国学者维尔纳德斯基、俄国学者梁赞诺夫斯基以及我国学者韩儒林、翁独健等人的支持。与之相对,另一位知名的苏联蒙古史学者贝勒津却认为“《札撒》决没有写成文书,由轻率的人们的谈话,将民间传话误当成了成文法典”(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札撒〉》,《蒙古学研究参考资料》第18辑)。后来,此说得到英国学者大卫·摩根的响应。
从法的演进规律来分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规范之一,法的形成一般要经过氏族习惯、习惯法到制定法的孕育和成熟过程,蒙古民族自不待言。又因法的内在属性在于强制力的保证实施,故我国古代亦有“大刑用甲兵”“刑始于兵”之说。从法的发展史和内在属性来看,成吉思汗令子子孙孙不得更改的训言、军令、民族习惯及宗教禁忌等,皆可被视为广义上的“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不仅发展时段不同,而且其呈现方式也难以划一。即便如此,这并不影响蒙古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然有一种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的存在。只不过,这种规范当时尚处于少经采摭的习惯法阶段。
元代法律体系变化及其争论
元朝初立,法制阙如,中原汉地曾用亡金《泰和律》断案。至元八年(1271),在建国号为“大元”的同一天,元世祖忽必烈诏令禁行《泰和律》。至元二十八年,元朝颁布了自己的第一部官方法典《至元新格》。然而,该法“虽宏纲大法,不数千言”(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李修生:《全元文》第40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存在过简的缺陷。有鉴于此,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再令重臣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元史》卷28《英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28页),既成,颁《大元通制》。二十多年后,监察御史苏天爵又上《乞续编通制》疏,请求对《大元通制》进行增减、删修,至正六年(1346),元顺帝“颁至正条格于天下”(元史》卷41《顺帝四》,第874页),为元代最后一部官修法典。
长久以来,人们对元代几部官方法典的正统性表示怀疑。朱元璋有一种流传甚广、影响甚巨的观点,曰“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阔,上下无等”(《明太祖实录》卷176,第2665页),从政统、道统两方面对元法提出了批评。其一,政为法本,明初士人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开篇即对元朝的正统性提出质疑。朝代更始,必颁新律,政统正当性自然影响到了法典的正统性,成为明人诘难元代法典的第一个理由。其二,从汉时起,中原汉法就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魏晋隋唐之律典,莫不以贯彻“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后汉书》卷46《陈宠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54页)的礼法精神为宗旨。元法则为另一番景象,元代实施“各依风俗”的治国策略,既不特崇奉某一种信仰,亦对各种宗教没有偏见,故礼法、道统主题并非元代立法的唯一指导精神,这也成为中原士大夫质疑元法的第二个理由。
再者,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元法与唐宋律典的制定程序也有显著的差异。我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民主制中“临事制宜”“随事立法”的传统对元代法律观念影响至深,是以建立在国俗民情之上的元代律法与传统中原律典的表现方式迥异。蒙古旧制,成吉思汗立国时曾令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惩治全国盗贼、审断词讼,“凡失吉·忽秃忽和我商议制定,在白纸上写成青字,而造成册子的规范,永不得更改!”(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二〇三节,台北联经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成吉思汗之制诏、大断事官断案之先例均对之后的日常司法审判具有约束作用,形成了元代法文化中审理诉讼“议事以制”的传统。元世祖即位以后,旧制虽因“祖述变通”而因革损益,但律出圣裁、中书的权力格局仍相沿不改。元代中后期颁布的最后两部官方法典,在编排框架上虽借用了唐宋律令的篇目名称,但奏对式的法律条文形式,与唐宋式的依据一定的立法程式而产生的律文或敕文,两者异质色彩明显,元初士人胡祗遹将此概括为元代“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胡祗遹:《论治法》,李修生:《全元文》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所言极是。
元代法律文化整合的实现方式
指出不同,并不意味着将差异绝对化。蒙元帝国早期法律文化发展程度较低,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亚欧大陆各自立国后,各个分支汗国都出现了文化上的本地化倾向。在中国,不少元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接受过儒家文化的浸润,仁宗、英宗父子在位期间一度出现“以儒治国”的施政倾向。在元代的官方法典中,忽必烈虽出于政治考虑禁行了以《唐律》为范本的《泰和律》,但并不反对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经过中书省审核或奏准的前朝“旧例”,故元代大儒吴澄认为元代法典与中原传统律典的关系是“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吴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而作为元代前中期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汇编,《元典章》的编排目录以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篇。此后,这种六部分篇的体例竟被以《唐律》为宗的《大明律》借鉴延续了下来,其中亦受《元典章》与中原传统律典、令典文辞虽异、意义多同的内在因素影响,为元明法律继受成功之一例。
明初修律活动频繁,其规模较大者有三次。朱元璋政权的吴元年(1367),丞相李善长等受命制定律令,李善长等主张历代律令集大成于唐,于是仿照《唐律》定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初步建立起明代律令的雏形。洪武六年,朱元璋又令刑部尚书刘惟谦修定《大明律》,此次修定后的律令,其“篇目一准于唐”,曰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认为经过修订后的《大明律》仍未很好地贯彻宽简适当、轻重适宜的立法初衷,令翰林院会同刑部再次修律。洪武三十年,定本《大明律》始颁行天下,成为有明一代定制。
在形式上,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的《大明律》与吴元年、洪武六年律相较,一个显著的差异是改变了过去唐律十二篇的分类,改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分类格局。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但有两点需要格外重视。其一,社会发展是推动法律演进的根本力量。我国古代律典的孕育、发展和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唐《永徽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古代封建律典的成熟。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在制定律典时,虽多以唐律为范本,但总归会结合当朝的现实条件而展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如唐前期重律、后期侧重于格;宋代偏重于敕;元代倚重于例;明清两代则律例并行,此所谓法在法外、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法的存在。其二,文化传统是法律发展进步难以忽视的渊源之一,这对于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尤其如此。法律体系的形成确是一个走向相对封闭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始终会有一些多元文化的、互有差异的法律习惯、概念和制度被吸纳进来,形成新的法律传统,并成为日后本国法律体系发展的本土资源。以上两点认识,对于阐明《大明律》在篇目形式上的变化大有裨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明律》篇目形式的变化是“适应洪武十三年改革官制后中央政务分属六部的政治体制的态势,吸收了唐六典、元典章以职官分类的法典布局格式的长处”(怀效锋:《大明律点校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点校说明”第2页)。
蒙元肇起漠北,其法律传统与中原差异明显,但当统治中心南移之后,在法律体系与内容两方面借鉴、融合汉法的趋势日渐明显。这种融合虽未全部完成,但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成果却逐渐融入中原法律文化传统,成为明清两代律典编纂的渊源之一。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融合,实际上也是人们对共同政治空间即国家实体认同的一种客观反映,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法律思想观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17ZDA1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