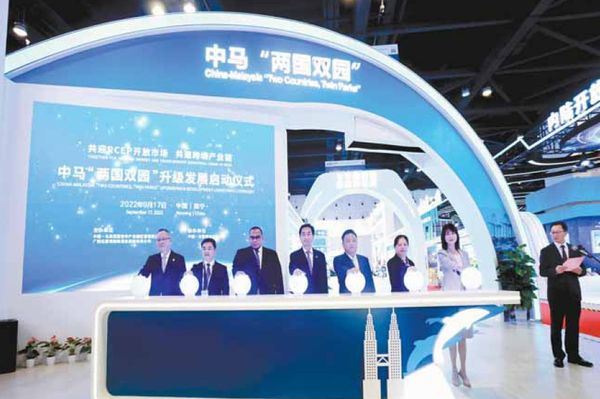曲折的归队路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前夕,我和同班的叶万松、张绪球、郎树德住在38斋508室。本应在1967年进行的毕业分配,一直拖延到1968年夏天,而且考古班的分配方案中,既没有一个北京的名额,也没有一个是去文物考古单位的,全是分到各省部队农场或农村先去“劳动锻炼”,然后等待“再分配”。我们四人被分到河南、湖北、甘肃、四川四个省,今后能干些什么,全然不知。

分配方案还未最后公布,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整理行装,把本来就很少的学生家当精简到极限。除了几本舍不得扔掉的油印考古讲义等教材图书之外,大家一起把小报资料传单书籍,也有不少业务书,统统卖到了废品收购站,一共卖了十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因为那时的全额助学金也好像才有十八块五,除去伙食费还能剩点零用钱。拿到这些钱,大家决定到外面好好吃一顿。
我们跑到前门大街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一只烤鸭(八块钱)和一些酒菜,把钱花光,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去乘凉聊天,言语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临别赠言,只有莫名的失落和迷茫。正在这时,大喇叭里传来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听到这些,我们更增添了伤感的情绪。最后相互无奈地说了句“好好去接受再教育吧”,就结束了“最后的晚餐”,各奔东西了。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再教育改造好了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忘掉专业”。好像我们几个都没有“改造”好,“劳动锻炼”近两年,又被分到偏远地区干了几年杂事之后,还是千方百计联系想调到文博单位去搞考古,但都进展不大。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开始恢复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北大的老师为了我们能归队都帮了大忙。2014年春节,我写信询问此事详情时,李伯谦老师于2月1日的回信中谈了当时的具体情况:
1971至1972年到故宫参加出国文物展览的筹备工作,当时北大的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都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大家,北大考古毕业的学生都分哪去了,全国的考古工作这么缺人,你们能否搞一份名单出来,局里想办法让他们早日归队,调回文博单位。我们知道61、62、63、64几届考古班学生大部分都在地县,许多是在政工宣传部门工作,商量之后,就由我执笔把知道下落的考古毕业生写了一份材料交给王局长,以后这些学非所用的人就陆续回到考古文博单位了。
李老师这些平和的叙述,却成为改变我们许多人一生命运的关键。据悉,王冶秋局长把“考古人员归队”一事,正式写入了给国务院的“出国文物展览报告”,经批准后转发到各地,文物局又把一些未对口就业的考古人员的名单交到各省。我和范桂杰就是1972年底由四川省组织部门下调令到“三线”重点地区的西昌和渡口,再发到县区,通知我们直接去省文化局报到,再安排到省博物馆开始搞考古的。考古班同学大部分也陆续被调到相关考古部门,我们38斋508室的四位室友分别到了洛阳、荆州、甘肃、四川考古所或博物馆,各自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这已经是毕业后四五年乃至十来年之后的事情了,其间有的颇费周折,还有些同学始终未能如愿。此事要惊动国务院才办得到,可见当时专业对口之困难,早日归队之幸运。在衷心感谢师长们对我们的培养和帮助的时候,我也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决心一定要努力做好这项既是爱好和兴趣,又是事业与责任的工作。
川西考古记
1973年初,我归队到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搞考古,最初的十多年主要是在川西地区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每年常常是一半多的时间在跑野外,既有辛苦和劳累,又有乐趣和收获。
汉墓与汉画
川西地区最多的地下文物可能就是汉墓。我第一次的考古工作即1973年三四月份跟王家佑、李复华、刘盘石一起去郫县竹瓦铺发掘东汉石棺墓。那里出土了多具画像石棺,上面刻着双阙、西王母、牛郎织女、午乐傩戏等大量汉画。他们仔细地给我讲解汉画的内容,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单位看我的发掘能力还可以,1973年9月又派我和戴堂才到乐山大佛湾去发掘汉崖墓群,为全省文物工作会准备考古参观现场,在大佛寺住了半个多月。乐山文管所的汉代出土文物极为丰富,雕刻着汉画的崖墓漫山遍野,使我大有收获。此后,我又从成都到阿坝,从德阳、绵阳到大邑,相继调查发掘了多处汉墓。
1977年,我爱人袁曙光调到省博物馆后,长期在保管部负责保管砖石类文物,对画像砖画像石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她发现汉墓画像中“阙”的图案很多,可能不是地方官吏才可以享有的。大量阙画像的分散出现,说明这种图案已经广泛出现在百姓的墓葬中,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此外,还发现汉画内容在墓内的分布也有规律可循。
我也开始注意研究这些问题。后来在三峡考古时,发现巫山汉墓中出土了数件刻有“天门”榜题的鎏金铜牌,安装在棺头上,说明四川汉墓中的大量画像很有可能是被古人布置为死后可以“升天”,在“天门”之中的天国上享受美好生活的场景。我又去考察了简阳鬼头山出土的画像石棺,不但证实在双阙画像上方有“天门”榜题,而且在其他十余处榜题的旁边,看到了与榜题内容相关的各种画像,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国胜景。
袁曙光还进一步把各地已发掘的汉墓中画像砖与画像石的排列组合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找出了其中的规律。我们将这些新的认识,合写了一篇《“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的文章,发表在《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得到圈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随后,我们又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袁曙光还根据这种观点,撰写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四川汉画像砖卷》的“概论”。汉画学界的同仁从此常常打趣地称呼我们为“袁天门”“赵天门”。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