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曾拜访一家医院新设立的托老中心,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幕终身难忘的场景: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内,日光灯照得四壁雪白,唯一的声音来自屏幕闪烁的电视。六张床依次摆开,每张躺一个人,只一张除外——一个阿婆背对电视坐在床上,蓬乱的白发在逆光中格外耀眼。她的脸隐没在暗影中,她的目光像溺水的人摸到一片浮木一样直勾勾地望向我。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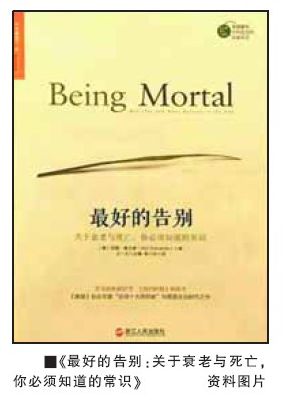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关心社会与人类境况的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们是否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美籍印度裔著名医生和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的作品《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以下简称《最好的告别》,本书中文版已于201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思考和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本文将以“照护”(care或caregiving)观念为中心介绍这本书。
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哲学议题
照护是指由经过训练的医疗专业人士或普通人向有需要者提供的,旨在治疗疾病、增进健康或提高生命质量的活动,包括三个主题:病痛(sickness)、衰老(aging)和死亡(death)。对一般人而言,这三个主题并不仅以个别、偶然、短暂的形式出现,而是贯穿个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从出生到死亡,人们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或某些时候求助于医学,接受照护,或为他人提供照护。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人们主要依赖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满足自身的健康需求;多数人将在医疗机构而不是家中走完人生的最终阶段。在这个意义上,照护不是一个只有医疗行业从业者需要关心的技术概念,而是一个与一切人类个体紧密相关的、基础性的哲学问题。
照护是医学哲学(philosophy of medicine)的中心议题。医学哲学作为一个新兴哲学分支,以医疗健康领域中的知识、伦理和过程为研究对象,以两个特点区别于哲学的其他分支。
第一,它集中体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连通性。医学以人为对象,以照护为本职。它不是纯粹的、“硬”的自然科学。它既有科学的一面,即医学科学(medical science),同时也有“柔软”的、人文关怀的一面,是“治疗的艺术”(the art of healing)。相应地,医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背景和取向,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科学哲学,是一个与伦理学、现象学、心灵哲学、社会哲学等哲学分支都保持活跃联系的领域。海德格尔对护理观念的影响、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都是医学哲学领域经典的“跨界”研究。
第二,医学哲学是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通道。自20世纪早期起,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兴起后,哲学作为学科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技术化倾向,成为“专门之学”。但是,随着医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我们意识到,哲学不能将自身隔绝于有关健康与医疗的公共议题之外。“照护”的观念不仅在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设桥梁,也由此连接其他哲学领域如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医学哲学或者说照护的哲学,追随的是自古典时代起哲学对人类心智与处境的道德承诺。
以上两方面共同塑造了医学哲学,使其表现出开放、富有活力、善于整合的跨学科特征,同时也使它具有无限潜力和广阔前景。
照护是为了良好的生活质量
以照护观念为中心的医学哲学的兴起,其主要动力之一是医学和医疗行业在西方工业化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强势地位。二战后以抗生素类药物为代表的一系列医学突破,使医生能够为人们提供非常有效的治疗,也使医疗行业从业者的职业权威和组织化程度不断上升。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生物医学(biomedicine)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当患者被看作一部待修理的机器,他/她的个体感受、认知、信念在医生眼中便没有太多正面价值,反而往往被视为治疗的障碍,这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这种情况下的照护,能在多大程度上忠于医学的初衷和制度设置的本来目的?
这一问题也引发了医疗界内部的反思。职业医生从事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写作和研究,是西方的一个传统。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是其中极富启发性的例子之一。作者基于大量访谈和真实案例以优美的文笔展示了对照护三大主题中的两个——衰老和死亡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应对衰老,包括老年医学(geriatrics)和养老。由于老年人在身体机能退化的同时往往身患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因此老年照护大多不追求治愈,而是设法妥善管理老人的健康问题。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医学高度发达的国家,老年医学却处于事实上的萎缩中。全美每年仅有不到300名医师选择老年医学作为职业方向,已无法弥补原有医师退休导致的空缺。老年医学从业医师的收入在所有医学分科中排名垫底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葛文德呼吁人们充分意识到,医学的目的不仅仅是确保人类的健康或生存(to ensure health and survival),而是保证良好的生活质量。
美国养老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的养老院(nursing home),遵循“保管”(custodial)式的运营思路,要求入住者在相当程度上让渡隐私和自主性(autonomy),将生活完全置于机构的控制之下,以确保其安全。另一类是以“辅助生活”(assisted living)为理念的养老机构,主张老年人可能而且应当在有条件地依赖别人的同时过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葛文德认为,后者体现出一种对个体自主性的更本质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面对死亡。医学科学的发展已经使死亡变得过于医学化。医生往往陷入过度治疗;患者与家庭不仅备受经济压力和折磨,也在死亡来临时缺乏准备。葛文德特别推荐的一个做法是医生、患者与家庭共同参与的临终谈话(end-of-life discussion)。这种谈话的目的不是让患者在这种或那种治疗措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了解他们的愿望,使人们对医学的各种局限性与可能性有明确了解,接受人终有一死的结局。研究表明,这种谈话能显著降低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治疗费用和痛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葛文德对安乐死(euthanasia)/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的保留态度。他认为,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之所以在已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发展缓慢,有可能是由于在这些地方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患者真正想要的并不只是“善终”(a good death),而是要维持良好的生命质量直至最后一刻(a good life to the very end)。而姑息治疗原本是指对那些身患不可治愈疾病的人们实施的控制症状(特别是减轻疼痛)、支持患者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措施。所以它不是一种仅适用于临终患者的照护措施,也不是又一个新的医学分科;它恰恰是照护本身,是一种所有医生在职业生涯中都应贯彻的理念。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照护
照护的观念是跨文化的,同时也与文化相关。葛文德的思考和《最好的告别》中讲述的众多故事基本以美国为背景。但其主题却具有一定的全球性意义。具体而言,《最好的告别》给我们的启示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医学的照护。在培养医科学生时增加与医学人文、特别是医患沟通有关的教学内容。中国医疗体制具有多元化的突出特点,即现代西医与传统中医在体制内并存,如何发挥中国本土医学照护传统的作用,是一个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方向。
第二,机构的照护。目前中国的养老模式仍以代际、居家养老为主。从居家养老向机构养老的转化,或许一定程度上也将在未来几代中国人身上发生。为了避免葛文德提到的一个社会的下层成员一旦无法从家庭获得足够照护,唯一的选择是进入条件恶劣的救济机构(poorhouse)的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认识到医疗市场化不是万灵药,均衡的顶层设计或能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
第三,哲学的照护。四种身份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身上重叠,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告别”之旅;作为现代人,我们的“告别”之旅是工业化世界带给人类的最大礼物和挑战;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独特的本土优良传统和制度设置;作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以上三种身份是我们运用自己的才智,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立脚点。照护有众多面向: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因素、医学模式、医患关系、患病体验、生命的意义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在我们面对自身与他人的痛苦时,推动着我们向人类的局限性迈出第一步的东西——勇气和希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