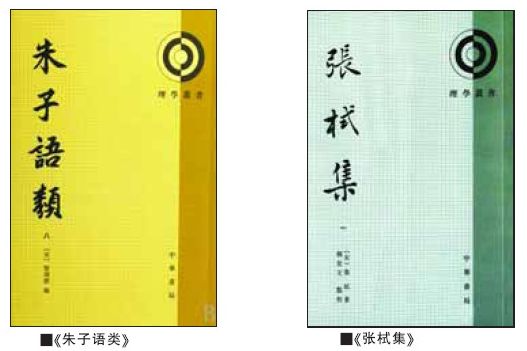

作为南宋书院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指向之一,“怡情”的创作指向在整个南宋书院创作观中有着颇为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文学创作的触发机制来看,这类“怡情”之作多为作者“内在期望”触发的结果,是作者自身“感悟吟志”的产物。从作品的内容和数量而论,这类作品多以书写南宋书院中人的日常生活为主,不仅是后世各种书院志中最为常见的,也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类。而从书院内外“怡情”之作的对比而言,南宋书院文学创作中的“怡情”指向在“怡情”体裁的选择、创作及批评实践的特征等方面既区别于书院之外骚人墨客“怡情”之作,又有着充分展现南宋书院中人“多重身份角色”的特殊意义。
感于外物 怡悦性情
对于两宋以前的士人来说,“怡情”体裁的选择似乎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论是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还是钟嵘《诗品》“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论述,其最终旨归均在于将诗视为文人墨客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心有所感时的最佳选择。
在宋代,这种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词体的逐渐兴起和不断发展,文人士大夫开始将“那些在诗中不方便表达的情感移之于词”(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以诗怡情”早已不再是时人感于外物、怡悦性情时的唯一选择。因此,“怡情”的体裁选择(“以诗怡情”还是“以词怡情”)便成为两宋士人开展创作实践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这同时也成为南宋书院中的讲学者和求学者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南宋书院中人而言,“以词怡情”却是一个几乎不被考虑的选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宋人相关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的角度来看,两宋士人在词体的接受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感情上接受而理性中排斥”(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的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秉承儒家传统文艺“教化观”,以“明义理”、“美教化”、“易风俗”为己任的南宋书院学者而言,这种矛盾和纠结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全宋词》中以“怡情”为创作指向的相关词作可谓不胜枚举,但南宋书院中人的相关作品却寥寥无几,这便是后者以儒家传统文艺教化观为准,从理论层面排斥词体的结果。
其二,就南宋书院中人以“怡情”为指向进行的创作实践而论,那些传世词作的水平亦远远比不上同题材的诗歌作品。如在张栻以“怡情”为指向创作的《水调歌头·联句问讯罗汉同朱熹》,其寥寥数语中即不乏“乾坤识易”、“渊冰语”等“理语”充斥其中,读来颇有“高头讲章”、“押韵语录”之感,而其同类题材的诗作《三月七日城南书院偶成》中则多有“林叶既敷荣,禽声亦融怡”、“层层丛绿间,爱彼松柏姿。青青初不改,似与幽人期”等融“情”、“景”、“理”于一炉的清新雅致之句,二者相较,可谓高下立判。
总之,无论是从体裁驾驭的熟练程度还是作品水平高下来看,南宋书院中人在选择“以诗怡情”进行创作时都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点亦成为其在面对“怡情”的体裁选择问题时更倾向于“以诗怡情”的另一重要原因。
体认自然 反对时弊
南宋书院学者以“怡情”为指向进行的创作,除在体裁选择上有所不同之外,还存在以下几个区别于书院之外同类作品的显著特征。
首先,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以“怡情”为指向的作品多为南宋书院中人日常生活的记述,既有书院学者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体悟,又不乏书院师生之间、师友之间相与出游的切磋交流。如以张栻《芭蕉茶送伯承伯承赋诗三章次韵》为例,全诗以“春去云藏岳麓”开篇,点明作诗时间是在春夏之交,而此时的湖南正是“梅黄雨涨昭潭”的时节,连日阴雨绵绵,令执教书院的作者在讲论之余颇有“政尔倚栏无那”的百无聊赖之感。此时忽然收到好友吴伯承感谢自己前日赠茶的回信和诗作,顿觉兴致盎然,于是挥毫提笔,和韵一首作为应答。全诗以“一瓯唤起清谈”作结,无一字言茶,而品茶之韵却尽在其中,令人回味无穷。宋人创作的六言诗不多,其中堪称佳作者更是寥寥无几,而后世批评家在评论张栻诗作时多以“清新醇雅”誉之,可谓中的之评。
其次,就作品“情”、“理”交融的情况而言,这些以“怡情”为指向的诗作大多能够在表现世间万物“生机意趣”的同时充分展现作者对“自然之理”的体认。如以朱熹《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为例,从表面上看,作者戏仿民歌之作,以明快之笔描绘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的清新雅致之景。但以“情”、“理”交融的角度观之,则全诗以“棹歌闲听两三声”作结,看似闲来之笔,实则其中所蕴含的“万物静观皆自得”之理却需要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和体察。
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书院学者多能够将自身对“理”的体悟作为媒介,以清新自然之笔来展现自己澄澈透脱的心胸与闲适恬淡的情致。而这种注重“情”、“理”交融,透过事物外在表象来探究其内在规律和精神实质的创作特点亦是南宋书院学者“怡情”之作的又一重要特征。
最后,从批评实践的角度而论,南宋书院的学者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对于“所怡之情”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一是要求“所怡之情”必须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情”,而非过分拘泥于推敲字句、炫技逞博的矫揉造作之“情”。这一要求既是基于写作者表达自身情感的需要,又是反对诗坛弊端的需要。联系当时诗坛的发展情况可知,当时的诗坛为江西诗派的影响力所笼罩,而相当一部分初学者在学习江西诗法时亦普遍存在流于表象的模仿,甚至将“使难字、用僻典”视为作诗之制胜宝典和不二法门。因此,如何纠正这种盛行于文坛的炫技逞博的矫饰之风,便成为摆在南宋书院诸位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直致心辞 陶写情致
执教或求学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常常将对矫饰之风的批判和对诗文作品之“真情”的提倡结合起来,在批判时人诗文之“狂怪雕锼”及“神头鬼面”(朱熹语)、“聱牙屈曲,波谲涛诡,艰深蹇涩”(方逢辰《诚斋文脍集序》)的同时,特别赞赏那些能够抒写作者之真情的“直致心辞”(欧阳守道《李瑞卿诗序》)之作。其用意便在于提示后学者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必须注重自身“真情”的抒写,唯有如此,才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关注对作者真情的体味和共鸣,进而收获感动人心的力量。
同时,书院文人还要求“所怡之情”必须做到“发而皆中节”。这既是对先秦两汉以来儒家文论要求文学创作应“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传统的继承,又是针对时人诗文创作中“不能皆出于情性之正”的文坛现状而发。诚如前文所述,南宋各书院的学者在涉及创作观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或有分歧,但从整体上均对文学的教化价值功能非常重视。换言之,这种以“怡情”为指向的创作亦肩负着“讲明义理”、“美教化、易风俗”的责任——这就要求写作者“怡悦性情”之时必须坚持以“中正”为准,使其情“发而皆中节”,避免“陷于异端”。
李春青在《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中指出,“‘文人’是一种文化身份,是一个人许多面孔中的一副,或者说是一个人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中的一种。”综合上文所述,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这些执教或求学于南宋书院的学者所展现出的是有别于史书中“以古圣贤自期”(《宋史·张栻传》)、“慨然有求道之志”(《宋史·朱熹传》)学者形象的“另一面”。因此,这种创作指向既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士人多重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展现,同时亦说明这些学者虽在日常的书院教学中时有“重道轻文”之论,却在内心深处依旧葆有对“文”的情感联结,甚至依旧将吟诗作文视为陶写自身情致的重要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对南宋书院“怡情”创作指向的分析和讨论亦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南宋书院学者“刻板、固执、轻视文学创作”的固有印象,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南宋书院的创作观。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